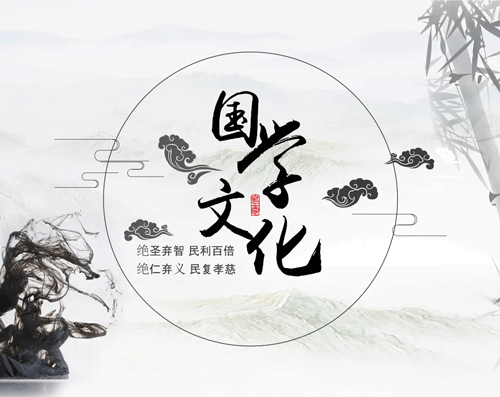基督禅与佛教自觉
发布时间:2023-09-06 11:22:11作者:互动金刚
20世纪60年代初,天主教召开“梵二会议”、主张宗教对话,当时,西方的天主教徒开始酝酿如何能把禅与灵修相结合。1971年,耶稣会士乔史顿(william johnston)发表专着《基督禅:冥想之道》,这部像是作者内心独自的着作,首次提出“基督禅”(christianzen)的说法。时至今日,这个说法已有近40年的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禅修方法,基督禅是为基督徒而设,并不是让他们放弃基督教的信仰,而是要让他们多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信仰方式,强化他们对天主、上帝的领悟。
在传统的东亚社会,佛教并不热心传教,甚至有些“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味道。然而到了欧美国家,从铃木大拙(1870一1966)开始,佛教一反常态,积极弘法。“基督禅”的出现,一方面是天主教徒主动学习禅法的结果,同时也是现代佛教主动弘法的结果。特别是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佛教与基督教一起探讨现代社会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进行有意识的宗教对话,促成了当前西方的“参与佛教”(engaged buddhism)。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缘此着手“本土化”的实践,在西方国家兴寺造像,涌现了一批“洋和尚”,开办禅修中心,参禅传法。
本文在解释何谓“基督禅”之余,试图说明:“基督禅”的出现,刺激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也就是佛教在现代社会的主体意识,表现为现代僧团的弘法主动性,以及亚洲佛教在西方社会的本土化实践。
一、“援佛入耶”的新尝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华的传教士,有不少参与翻译佛经、以英文介绍中国佛教。譬如,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 d,1845—1919),这位着名的英国传教士在杨文会(1837一1911)的建议下,英译《大乘起信论》。两人最初的合作很愉快,但是,李提摩太更关心的是如何以基督教的思想来诠释《起信论》,这引起了杨文会的不满。当时的中国佛教界,无法容忍在佛教里掺杂基督教的因素。李提摩太的心态,是想以基督教包容佛教。这种“援佛入耶”的方式,与唐代景教借佛教推广天主教的传播策略有所不同,但是最终也没有成功。

时过境迁。“二战”以后到日本的传教士,因与日本禅师交往密切,耳濡目染,切磋禅法,提出了“基督禅”的构想。这个设想,很快得到了日本及欧美佛教界的认同。乔史顿1925年生于北爱尔兰,1951年加入耶稣会到日本传教。在日传教20年,缘此写出自己的心得《基督禅》。他在书里说,长年的坐禅,或与禅师的玄谈,深化了他的基督信仰。
“基督禅”的确切说法,应是“基督徒的禅”,也就是借用“禅法”服务于基督徒的灵修。禅并不只属于佛教,基督教亦可有自己的禅法。乔史顿说,基督教可以在东方禅师的帮助下挖掘与发展自己的禅法。现代社会的特点之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禅修的目的是要关注或反思个人(自我)的意义与存在,而在犹太一基督教传统里,“冥想”须以“上帝”为取向。乔史顿认为,基督教若要适应现代人的需求,灵修的方式应当借鉴以“个人”为中心的佛教禅法,从而有必要发展属于基督教的禅,即“基督禅”。这与当年的李提摩太不同,乔史顿的“援佛入耶”并非是要包容或取代佛教,而是想用佛教推动基督宗教晌现代发展。
1965年10月,天主教“梵二会议”发表《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正式承认其他宗教的思想与社会文化价值,整个基督教世界有意推动普世性的宗教对话。1962年11月18日,罗马教皇在他的图书馆里接见了28位日本禅师,并说,罗马天主教与佛教都是为了和平,改善人类,荣耀上帝。葛兰汉(dora graham)在他的序言里特意提到此事,表明他在1963年发表的这部《禅的天主教》,确实是在呼应一种时代的需求。乔史顿1971年发表的《基督禅》,直接探讨属于基督教的禅修方法;拉萨尔(h.m.lassal le)在1974年发表《基督徒的禅观》,亦是专门解释“基督
禅”。此后涉及“基督禅”的文章或专着,频频问世。最近的十多年里,肯尼迪(robert e.kennedy)出版《禅的精神、基督的精神:禅在基督徒生活里的地位》,试图说明成为天主教徒的新方法;2003年鲍威尔(robert powell)还出版小册子《基督禅:耶稣基督的基本教义》,借用佛教“不二”的思想,强调“教会”与“天国”的一致性,只是这种“一致性”、“无分别”受到了世人的漠视。在他看来,禅修所要觉悟的对象,亦是要与“真实自我”达到无分别的境界,而基督体现了“真实自我的完整性”(oneness of the real self)。
这些信仰基督的西方人,关注佛教禅修的目的,并不是要背离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们或是为了发展现代基督教,或是想给佛教徒传播基督福音,这些神职人员,特别关心“基督徒如何坐禅修观?”甚至还有天主教神父或新教牧师,主动创办“静修中心”,推动坐禅式默观。他们对东方的瑜伽、坐禅、静坐等很感兴趣,建议在祈祷时吸收坐禅观想的方法。他们认为,禅观的修持可以强化他们的祈祷生活,有助于灵性的成长。乔史顿的《基督禅》与《爱的内在之眼》,1990年被合为一部着作,题为《天主教会我们祈祷》,点出了基督教借鉴禅修方法的用意所在。
佛教的禅法,至少能在两个环节有助于基督教的灵修。首先是能为基督徒舒缓生活的压力,调适身心。现实生活与宗教观念,经常会有一定的冲突,而佛教主张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一致不二,禅宗向来是把日常生活作为修行的道场,语默动静、坐卧行走,皆不离禅,达到现实与理想的无分别境界。所以,禅修能改善祈祷者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释放祈祷者的内心压力。
第二方面,这是“基督禅”的最根本之处:基督徒借用佛教的“止观”、“数息”等禅法,形成基督教的“默观”方法,充实基督教原有的“默祷”。禅修的主要手段,是通过“调身”、“调息”、“调心”,从而“入定”,进行“止观”。止是止息散念,断除烦恼,净化内心;观是观想一处,证入清净。禅的原义是“静虑”,并非局限于佛教。但是,禅在佛教里,就是“止观”两字,代表了佛教两种最基本的禅法。基督禅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数息”的方法达到止观的禅境,观想天主,能在心灵深处见到天主,与天主结合为一,顿悟“天主是爱”。1995年克利福特(patricia h.clifford)出版的《静坐:与基督禅相遇》,解释了如何能在打坐时感悟上帝。
就“禅”的最高境界而言,修禅者要超越自我,体悟“无我”、“无相”。若能体验到“无相”的真实自我,这种体验类似于基督徒对上帝的经验。所不同的是,禅宗的顿悟是靠自己的智慧,所谓“自性自度”,而基督徒的体悟全靠上帝的恩典。如果能以这样的禅法去向上帝祈祷,也就是富有禅意的祈祷,基督徒就可成为“无相的祈祷者”(imageless prayer),放下自我,全身心地去感悟上帝。
所以,基督禅的重心依然是基督教的灵修,禅无非是一种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是基督教所要吸收的佛教精髓。像这样的“援佛入耶”,想借佛教的禅法来发展基督徒的灵修生活,特别是祈祷的经验,以便更好地适应现代人的精神需求。
二、作为治疗术的禅法
1927年铃木大拙以英文发表《禅佛教论集》(essays in zen buddhism),从此以后,禅在西方,特别是在知识精英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在正式出现“基督禅”以前,西方最关注禅宗的是精神分析学派,尤以荣格(carl jung,1875—1961)与弗洛姆(erich froinm,1900—1980)为代表。
1957年8月,铃木参加由墨西哥国立大学医学院精神分析系主办的学术会议,约有50名北美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与会,期间他与弗洛姆的讲稿汇编成《禅宗与精神分析》。弗洛姆分析了当代的精神危机,想要通过禅悟找到一条摆脱精神危机、解除压抑、获得幸福安宁的精神分析之路,认为“精神分析是对精神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禅则是一种精神拯救之路”。这种观念在荣格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努力要把作为科学的精神分析学与作为一种神秘之物的禅结合起来。1939年他为铃木《禅佛教入门》德译本。所写的序言说,要把禅移植到西方,那是不可能的。禅门的心灵教育,在西方根本就没有,但西方的精神分析学却能够理解东方的禅悟。荣格建议要把“禅”“严格地置于科学的范围内来了解”。现在还有不少的西方人想以佛教的禅修来补足精神分析学的缺陷。艾伯斯坦因(mark epstein)的《没有思者的思想:佛教的心理治疗术》,即有这方面的学术动机。
精神分析学在西方被认为是一门有科学根据的学科,“禅”在西方能与精神分析学相贯通,大大推动了禅宗在西方的传播。弗洛姆、荣格把禅宗所讲的“无念”、“无心”当作“无意识”,挖掘其精神治疗的意义。荣格提出,在“个人无意识”之外,还存在“集体无意识”,并以此来认识禅悟的独特性。在他看来,禅悟的时候,“无意识的弥补作用得在意识明朗化时显现,此际的心境既能转化,并解决痛苦的冲突”。禅宗所讲的无意识,亦即“无念”,实际上是一种朗然清明的境界,破除了心识的昏沉散乱,所以,这种解脱性的“无意识”,远比弗洛伊德所理解的压抑性的无意识深刻得多。“无意识”的发现,而且,在人的意识结构里,“无意识”的部分要比意识多,这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重要贡献,是对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有力冲击。他们之所以用“无意识”来理解禅宗的开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禅不能用哲学理性来解释,是神秘之物。
但在禅师看来,精神分析学所说的“无意识”,远还没有体现禅的本质。1958年久松真一(1889—1980)在与荣格晤谈以后说,荣格所说的无意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个体自我是无法认知的,但禅宗所说的“无心”(无念),不但可以认知,向且是“了了常知”;禅宗所说的自我,是已经觉悟者的自由自在的“自我”,所谓“本来面目”;精神分析所说的精神治疗,并没有触及精神的本来源头,而禅宗则要求当下一次断除,从一切妄念里彻底解脱出来。久松认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更像佛教所说的“无明”,而不是禅宗所讲的“无心”(无念)。不过,若就佛教在西方的传播而言,要是没有精神分析学的误读,禅宗在西方的影响就会减弱许多。
就西方人目前的兴趣而言,好些人还是偏重于汲取坐禅的技术方法,从而达到静心、催眠等心理治疗目的,甚至把这种方法运用到医学上的临床实践。特别是心理学家,他们主要是从精神治疗的角度来理解、接受东方的“禅”。他们要以科学的眼光说明“禅”的合理性,甚至以各种仪器测试禅修者的脑电波变化。这是典型的西方式误解,但这种误解为禅的传播奠定必要的基础。
精神分析学派把“禅法”当作一种治疗术,基督禅则是想用佛教的禅法来培育一种适合时代人心的基督教灵修方法,即把“禅”视为一种修行方法。基督禅的理解,显然还是基于宗教的需求,而不是像精神分析学派那样出于科学理性的考虑。这种理解植根于铃木大拙当年所说的“神秘主义”。
三、神秘主义及其超越
如何能让从不了解禅宗的西方人弄清什么是禅?铃木以“神秘主义”搭建禅与西方宗教文化的桥梁。他的《基督徒与佛教徒的神秘主义》(mysticism:christian and buddhist,1957),特别重视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1260一1327)的神秘主义思想,认为禅与基督教的默祷比较接近,坐禅类似于基督教的“灵修”,双方都有神秘主义的因素。比较佛教与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早已成了西方学者与宗教家的一项重要议题。
“禅”在英文里被译为meditation,原因是该词和基督教所讲的“灵修”相似。艾克哈特是德国多明尼哥会教士,融会了新柏拉图主义、阿拉伯及犹太哲学,是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代表人物。因受铃木的影响,欧洲的学者,最初几乎都把“禅”当作一种神秘的冥想。着名的宗教学家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曾给铃木1933年的禅学论文集写过序言,他在《论神圣》(idea fo the holy)、《东西方神秘主义》(mysticism:east and west)等书,断然否认禅是一种哲学,反对用西方的哲学理论来诠释禅悟。在他看来,顿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开悟的时候,修行者既无法自知,也无从预知。
神秘主义(mysticism),也被译为“冥契主义”,后者或许更能反映它的特质。这是宗教学家在描述宗教经验时最常用的概念之一。依据伊利亚德(mircea.eliade,1907一1986)的说法,西方的“神秘”(mystery)一词最早用于1545年,是指“未被人的思维认识过,或是人的思维不能理解的,超出了理智或一般知识认识的范围”;神秘主义往往源于“神秘的技术与行事”方式。奥托分析宗教的“神圣感”时说,“神秘感”是“神圣感”里的非理性主义因素,是宗教生活的根基,为此他生造了新词numinous(神秘者)。神秘体验,通常表现为与经验对象的同一或结合。这种境界,常被说成是难以名状、不可思议。
禅悟是要返观自身,领悟没有任何执着的自我,即“无相”、“无住”之我、无位真人,并且消除与周围世界的隔阂,即禅师常说的“打成一片”。铃木大拙传承的主要是临济禅,机锋棒喝,这种禅修的风格本身也已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杜默林(heinrich dumoulin,1905—1995),德国神父,1935年赴日本学习东方宗教,主要学禅,着有两卷本的《禅宗史》,被誉为20世纪最了解禅宗的两方人。他在1992年出版的《20世纪禅宗》一书里,追溯了基督教里的神秘主义传统。除了铃木大拙所讲的艾克哈特,还有12世纪的圣维克多·理查德(richard of saint—victor,1173年卒),把“神秘”看成是超越想象与推理的最高境界,在领受上帝的无相性(invisibility)前,先要认清自己无相的实在(invisible reality)。这种宗教哲学,主张要在静默之中祈祷,实现与天主的合一。基督禅,正是要用“观想”的方式去让祈祷者达到与上帝的同一,直接感受上帝之爱。
在铃木之后,京都学派的第二代学人,久松真一、西谷启治(1900—1990)都在他们的谈话、着作里提及艾克哈特这位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就在乔史顿发表《基督禅》前一年,1970年他发表了《宁静之点:反思禅与基督教神秘主义》。这个书名,表示了他要清理铃木大拙的精神遗产,呼唤一种新时期的神秘主义。后来他出的自传,亦被称为《神秘之旅》(mystical journey)。祈祷或灵修时的灵魂慰解,依赖于上帝的恩典。这在佛教看来,上帝的恩典属于一种外力拯救。禅宗发展到后来,明清以来,最主流的思想是“禅净双修”。“念佛”即是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同时观想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这是佛教所谓的“他力信仰”。基督禅的观想方式,更像是一种“禅净双修”。
然而,铃木大拙把“禅”说成是神秘主义,这种观点并不能说服所有的人。特别是铃木总把禅说成是“超逻辑”、“非理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强烈反对。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受到日本学者的鼓动,开始关注日本曹洞宗的开祖道元(1200—1253)禅师。临济宗与曹洞宗的宗风确有差异,临济宗素来喜欢“机锋棒喝”,曹洞宗则是“冷峻不露”。因此,与i临济禅的神秘主义不同,道元被塑造成理性的思想家或神秘的现实主义者。阿部正雄把他与欧洲中世纪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相媲美,傅伟勋赞叹他是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把他和海德格尔相提并论。到90年代,杜默林在评述“基督教与禅观”时,引述了道元“只管打坐”的理论。这位日本开祖很擅长总结,他的《普劝坐禅仪》被译成英文出版,竟为“基督禅”提供了更具体的坐禅方法。
道元的禅法,扩展了西方对禅的认识。在铃木所说的临济禅以外,西方发现了曹洞禅。相应地,禅的神秘主义色彩,得到了一定的消除。其实到8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对“禅”的认识与研究,已不再局限于禅宗,而是覆盖了中日韩三国佛教所有的禅修传统,尽管中国的禅宗一直最受关注。不过,7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基督禅”,并不重视理性主义的道元禅,主要关心禅的神秘主义色彩。
无论是以神秘主义形容临济禅,还是以理性主义描述曹洞禅,它们都为佛教与基督教的会通架设了桥梁。铃木大拙等东方禅师的弘法,是“佛基会通”这座桥梁的一端;西方天主教徒所提的“基督禅”,则是这座桥梁的另一端。基督禅的出现,让佛教界意识到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宗教间相互的沟通与学习,有助于佛教在西方的弘法实践。这种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推动了佛教在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进程。
四、宗教对话的倡导
主张“基督禅”的社区,通常同时欢迎天主教徒、新教徒,甚至还有犹太教徒、无神论者等。有的禅师借用“茶禅一味”的典故,对那些西方人说:不管我们把自己说成是佛教徒、基督徒,还是什么其他的宗教徒,我们现在请喝同一杯茶;我们不要多想,现在要的是静下心来。禅修需要的是“活在当下”、“用心体验”,而不是要用语言去说明修禅的终极意义。
基督禅所表现的佛教与基督教关系,是友善型的。但在铃木大拙,佛教在西方的弘法,主要是为了彰显禅的优越性。他以神秘主义作为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契机,阐发佛教的根本思想——无我、空性。西谷启治,这位曾经聆听海德格尔上课的日本思想家,想用佛教的“空”去超克西方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困境。在他的心目中,东方文化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未来方向。这很难说是一种积极的宗教对话,现代的学者称之为“反转的东方主义”,即以东方文化为中心,对西方文明持有一种浪漫的想象。
到了阿部正雄,京都学派的第三代学者,主要从事宗教的对话,在基督教的文化背景里,寻求禅宗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价值。阿部正雄到了美国以后,他以佛基对话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学术工作,享誉欧美学术界。1998年,在他80岁生日之际,美国出版一部颂寿文集《阿部正雄:禅的对话生活》,全面介绍了他从日本到西方展开佛基对话的经过与思想。这位长年在西方生活的日本学者,希望对话本身能对佛教与基督教双方有益,从而帮助佛教徒与基督教都能成功应付现代社会虚无主义的侵蚀。
20世纪的宗教学,宗教对话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在基督宗教的主流文化里探索宗教对话的理论与实践。而在佛基对话方面,北美自80年代以来,已有丰硕的成果可资借鉴。1987年美国成立“佛教一基督教研究会”(society for·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几乎每年要开年会。讨论的议题,往往是当前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譬如,2000年第六届年会的主题是“佛教、基督教与全球治疗”,内容包括:消费主义、全球伦理、冥想实践、环保、人权与社会正义、身心治疗、社会性别、经济压迫、种族压迫、抵制暴力、宗教仪式、文化、艺术、文学、媒体、科技等。我们从中已经看不到佛教与基督教互争高低的影子,而是共同探讨现代社会的治理与建设。
有了这样的研究议题,禅师的重任之一,是要把原本位于西方社会边缘的禅,推向西方社会的中心,使之成为一种参与社会的佛教,即“参与佛教”。这种佛教积极参加社会福祉的增进,热心慈善事业,改变了佛教作为一种出世宗教的传统形象。卡普洛(philip kapleau,1913—2004)是一位本土化了的美国禅师,他在《融会东西方的禅》(zen:merging of east and west,1989)里告诉西方的禅修者,在修禅的同时,还要成为一个好的犹太教徒或天主教徒,禅修并未遁世,亦要有助于社会。他只想让现在的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先去修禅,不要急于让他们改宗。禅在西方社会的作用,首先是要辅助于社会的治理与人心的陶冶。惟其如此,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东西方的融合”。
传统宗教与现实处境的关联,并不一定是完美和谐的,有时很有可能会互相冲突。基督教、佛教如何处理他们与现代处境的关系,基督徒、佛教徒的经验应如何介入、诠释现代的处境与经验,这对双方来讲都是莫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重要的已不是佛教与基督教的优劣比较,而是如何共同面对现代世俗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塑造人生的意义、价值与生活目标。理想的宗教对话,好像进行一场真诚的谈话,最终并不是要克服对方,而是要使双方接纳对方。禅宗乃至佛教,要想在西方社会长久传播,势必要有一番新的诠释,方能达到宗教对话的目的,从而融入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
在这场宗教对话里,佛教为基督教提供了一套新的灵修方法,基督宗教则是激发了佛教的入世精神,形成所谓的“参与佛教”。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佛教自觉,常以宗教对话为沟通手段,积极参与现实生活。
五、禅的本土化实践
当前西方佛教最活跃的地区是在美国,60年代是美国佛教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时期。据《大英百科全书》的统计,截止2005年,美国人口3亿,佛教徒272万,约占总人口的0.9%。美国佛教徒在1900年约有3万人,没有什么统计的意义;但到1970年佛教徒人数跃增到20万人,其比例为0.1%,实现零的突破,这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此后每年以8万多人的增幅递增,到1990年佛教徒的比例已达到0.7%。
美国佛教到1970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与“基督禅”的出现时间基本一致,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关联。基督禅,是东方禅师向西方传法、西方天主教徒主动学习的结果,因缘和合,水到渠成。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很快成为佛教界在西方弘法的重要理念,推进了佛教在欧美国家的本土化进程。伴随着大批禅修中心的出现,西方社会涌现了一批欧裔禅师,他们写的禅学心得,有些极为畅销,一版再版。
1893年芝加哥召开着名的“世界宗教大会”,日本的宗演(1859—1919)禅师与斯里兰卡的佛教青年达摩波罗(dharmapala,1864—1933),作为全球佛教代表与会,发言介绍禅宗的思想。宗演,因此被誉为“美国禅开祖”。当时的随从,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铃木大拙。铃木从1897年到1909年,一直在美国工作,为他后来的弘法奠定基础。到20年代,铃木的名字在西方世界已与东方的禅宗联为一体。他对西方的深远影响,不仅是他的临济禅解读,还因为他向西方介绍了基本的禅修方法。早在30年代,铃木出版《禅师修行》(training of the.zen monk)、《禅宗手册》(manuai of zen buddhism)等书,把禅师日常需要掌握的偈颂、经典文字、公案故事汇编成册。这些英文的禅籍,推动了禅在西方的实践,从此就有一批一批的西方人到日本学禅,其中既有传教士,也有宗教学者。
20世纪上半叶弘法的结果是,“禅”在60年代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禅”已经走出知识精英的小圈子,开始在西方社会产生实际的影响。在当时的美国社会,铃木所介绍的临济禅,成了美国青年反主流文化的一面旗帜。他们提出了一种“棒打禅”(beatzen),作为当时嬉皮士(hippies)文化的组成部分。50年代开始,旧金山、洛杉卫、纽约的艺术家群体刮起了一股“颓废”之风,这批青年自称是“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或“垮掉青年”(beatniks,又译“避世青年”)。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垮掉”,而是一批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抱有怨气的“愤青”,崇尚无政府主义。他们中间有一批人成了禅宗的信徒,这些厌恶战争、鄙视消费的美国青年,在神秘莫测的“禅”里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看似悖谬的禅宗公案实际上是对习惯思维与理性思考的反动。当时美国最着名的禅宗学者沃斯(alan watts,1915一1973)发表着作《棒打禅、方正禅与禅》,而他被认为是美国继铃木大拙之后弘扬禅法最有力的一位。
先后陷入“韩战”、“越战”的美国,1965年颁布“移民法案”,引发亚裔移居美国的浪潮。这是美国佛教在60年代得以急剧发展的直接原因,到1970年几乎已经包容了世界上所有的佛教修行传统。日本佛教、中国佛教在美国的传播,这时也有很快的发展。铃木大拙从1950年到1958年重回美国,在大学与城市间频繁讲演。日本禅师建立的道场,此时声誉雀起。譬如,铃木俊隆(shuntyu suzuki,1904—1971)的“旧金山禅修中心”(san francisco zen enter)、前角博雄(hakuyu maezumi,1937—1995)的“洛杉矶禅修中心”(zen centerof los angeles)。特别是前角博雄,被认为是继铃木大拙之后对美国佛教影响最大的日本禅师。中国禅宗在美国的弘法,首先要数宣化上人。这位虚云老和尚的弟子,是沩仰宗第九代接法人。1959年他到美国成立“中美佛教总会”(sino—american buddhist association),后来改名“美国法界佛教总会”,现有万佛城等着名的道场。70年代以后,台湾的大和尚陆续前去弘法。1976年星云大师组团访问美国,1988年在美国建成“西来寺”,被誉为“西半球第一大寺”。据不完全的统计,目前美国约有125家华人佛教组织,半数以上是在加州,约有五分之一是在纽约。
所有这些东方禅师的道场,要想在欧美国家生存与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是“本土化”。基督禅,是众多本土化策略里的一项重要方法。越南裔的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nh),主要在法国生活与弘法,现在经常到美国活动,他的着作风靡欧美,在一般书店都能找到,其影响力不亚于当年的铃木大拙。他的《生生基督世世佛》。出版以后极受欢迎,是西方许多禅修中心的推荐读物。
欧美现在有一批能够着书立说的西方禅师,他们多半先向日本禅师学习坐禅,绝大多数还去过日本禅寺体验生活,然后回到西方开设禅修中心,授徒传法。有些禅修中心现在已成规模,在西方社会很有声誉,譬如卡普洛的“罗彻斯特禅修中心”(rochester zen tenter)。这家中心是他1966年从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创办的,成员已经遍布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乃到欧洲国家;它的分支机构甚至开到了瑞典、芬兰、新西兰。西方禅师兴办的禅修中心,通常主要是直接面向西方人,弘法对象绝大部分是基督徒。所以,他们的弘法,必须能沟通禅与西方的宗教与文化。卡普洛在日本拜过三位禅师,1965年剃度出家。他的着述丰富,尤以《禅门三柱》(three pillars 0f zen)、《融会东西方的禅》在英文世界最为着名。美国还有一批本土的禅师,譬如1989年出版的《禅在美国:五位禅师与美国佛教的追求》,介绍了艾肯(robert aitken)、孔威廉(jakusho kwong)、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斯图亚特(maurine stuart)、贝克(richard baker)等在美国传法的事迹。
今天,打坐修禅在美国青年当中已经失去了反叛的意味,渐渐成为他们的一项生活习惯,美国的不少大学生乐此不疲。当然,相对于西方的主流文化,能坚持禅修的学生并不多见,绝大部分还是亚裔或新移民,欧美本土的学生很少。
结语
佛教在欧美的未来发展,本土化是唯一的出路。“基督禅”是禅宗与基督教深层对话、相互融合的产物。这个理念的提出,推动了欧美国家的佛教自觉,宗教对话成为全球化时代佛教传播的基本方法。基督禅,这是一首神父、牧师与禅师共同演奏的交响乐,融合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禅”在西方人的心目里,除了一如既往的神秘色彩,现在平添了一份生活气息。禅在西方社会,已经不再遥远;佛教也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进入西方社会,关注现实人生的问题。
探讨佛教在西方社会的本土化,也就是讨论佛教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当然,“现代化”着眼于时间的变迁,而“本土化”重在地域空间的转化。就在一百年前,佛教徒在西方传教士的眼里,不过是需要拯救的异教徒。基督禅的出现,表明东西方的这两种宗教有了全新的沟通方式。未来的中国佛教,将要如何面对开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