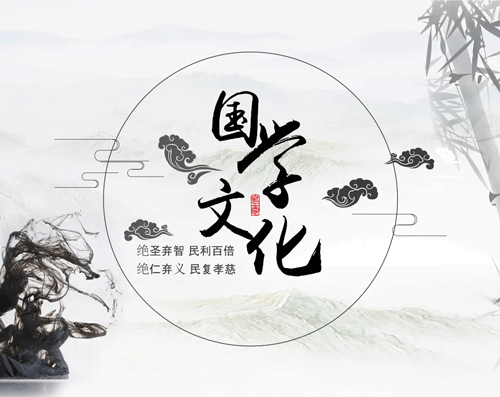女性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应提到思想史的高度
发布时间:2023-09-08 12:10:41作者:互动金刚

导语:女性在佛教信徒中占有绝对多数的现实,与女性在佛教出家僧团中的从属性地位之间,其落差之大,确实十分显着,也令以倡导男女平等为伦理准则的当代世界颇为费解。而这一现状的形成,其源头在于着名的“八敬法”。
刚从宝岛台湾参访法鼓山、慈济功德会、佛光山和中台禅寺回来,就碰到两件事情:一是单位里的女同事们正在兴致勃勃地准备着出游,自娱自乐地庆祝她们的节日;二是庵堂中的尼僧们正在热热闹闹地张罗着为百岁老师太观性法师举办寿诞。由此,我猛然想到,全世界女性的节日——三八妇女节即将到了。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全世界佛教信徒中,女性占了绝对的多数。回顾此次访问台湾,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台湾四大道场的中坚力量,基本系女性出家众。确实,佛教与女性之间的缘分实在是十分深厚的,也是源远流长的。
其实,佛教从最初的创觉者世尊出发,到由世尊所创立的僧团,都是一个基本由男性所主导的宗教信仰世界。从佛教史料的考证角度分析,直到世尊圆寂后五百比丘进行第一次结集之际,在佛教僧团中,尚未见女性的踪影。根据《大爱道比丘尼经》的记载,比丘尼的出家,始自佛陀出家成道后十四年,佛陀的姨母,也是佛陀实际上的养母摩诃波阇波提,即大爱道女,在佛陀回乡省亲之际,向佛陀请求出家为尼僧,但未得佛陀应允,后经佛陀的堂弟阿难的再三说情,据说她还发誓谨守“八敬法”,才勉强被佛陀接纳,僧团中始有尼众,这可谓是尼众僧团之滥觞,由此,大爱道女成为历史上第一位比丘尼。但此段记载与阿难尊者出生于佛成道日的记载,在时间上不相吻合,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而中国的出家尼僧则是滥觞于西晋时代,距离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三百余年了。《比丘尼传》卷一记述到:西晋建兴年间,即公元三一三至三一七年间,尼僧净检随西域沙门智山剃发受沙弥戒。升平元年即三五七年二月,请昙摩羯多立比丘尼戒坛,净检等三人共于坛上受具足戒,这是中国比丘尼僧团的开端。而发展到如今,在汉传佛教流传的地区,大陆和港澳地区虽然有相当数量的尼众道场存在,更有以隆莲法师和她老人家的法子如意法师、如瑞法师为代表的尼众精英,在中国的佛教界已经并正在继续发挥着意义深远的影响。由她们所创办的尼众佛学院,以及福建、上海等地的星罗棋布的尼众学院,正在为中国佛教界培养造就新一代拥有良好文化素养、精深佛学造诣、虔诚精神信仰的尼众队伍;但从总体上说,大陆中国的尼众法师继续以“二部僧”的角色,在中国大陆的佛教界处于配角地位。这与我国台湾地区尼众法师在四大道场逐步走向寺院主角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在台湾佛教世界中,证严法师作为比丘尼领袖和事业成就者,昭慧法师具有深邃思想、义理根基、引领佛学之思潮而着称;如此的景象,在世界各地汉传佛教流传地区尚未出现。
众所周知,女性在佛教信徒中占有绝对多数的现实,与女性在佛教出家僧团中的从属性地位之间,其落差之大,确实十分显着,也令以倡导男女平等为伦理准则的当代世界颇为费解。而这一现状的形成,其源头在于着名的“八敬法”。问题是,以倡导“众生平等”而名震寰宇的佛陀,在其深邃的教理中,理所当然的对男女平等持肯定态度;但事实上,由佛陀对自己姨妈的出家这一事件的顾虑重重,以及流传于世的“八敬法”,无疑给人以男女不平等的印象。对此现象如何理解,似乎是了解女性与佛教之关系的一个重要结点,此结不解,就无法心悦诚服地接受佛陀的男女平等观,更进一步难以服膺于佛陀的众生平等观。
在台湾,关于“八敬法”的争议,到目前尚未尘埃落定。此争议发轫于2001年,由台湾具有相当学术修养、并且特别重视社会公益、在教界拥有相当地位的昭慧法师发起。她系一代佛学泰斗印顺导师的弟子,对于佛教教理有精深的研究和相当高的造诣,特别难能可贵的是,昭慧法师具有无限的悲悯慈心,关心社会公益事业,能够将严谨博大的佛教哲学思维与身体力行的济世情怀圆融结合,很少有男性宗教领袖做的如此天衣无缝。昭慧法师在2001年4月发表的《八敬法显非佛说》的文章中。以犀利的笔法列举三大理由以证明“八敬法”非佛说:
第一、佛陀在世时,就以极其开明的态度,打破弟子对他“个人崇拜”的迷思……毕竟所有经典都不是佛在世时逐字记录的。佛灭之后,经典的结集权与解释权,又都掌握在男性手里。
第二、退一步言,即使在当时当地为“维持僧团秩序”而制定之法,一旦时空背景不同,反而会造成僧团两性的对立,就应予以废除,这就是遵循佛陀遗教“小小戒可舍”,而不是违逆佛戒。
第三、就以戒学原理而言,也可肯定“八敬法非佛制”,原因是:(一)、八敬法非“随犯而制”,独独在尼众尚未出家前就预制在那里,连罚责都订好以伺候未来之不依从者,实在太例外了。(二)律典中记载比丘尼不行八敬法应受的惩罚与更古老的戒经冲突。(三)所谓“比丘尼不得说比丘过,比丘得说比丘尼过”来源可疑,亦与以往史实不符。(四)“比丘尼不得骂谤比丘”,这是多余的。(五)最不合理的就是:“受具百岁,应迎礼新受具比丘”。根据以上情形,显然原是僧尼团刚成立时,佛陀交代比丘们担任教师,所自然产生的“师生伦理”,却不幸……形成“两性伦理”。
我对未来中国佛教抱有很大的愿心,同时,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尼众学院从事尼众教育工作,因此,对于尼众的力量也特别关切,对尼众在未来中国佛教事业中的作用寄予殷切的期望。但想到“八敬法”,就使我感到困惑,因为“八敬法”的规定,使尼众失去了独立性,变成了男众的附属品,比如受戒、出僧残罪、安居,以及作见、闻、疑三自恣,均要向比丘僧中作,把尼众的一切行事作法,全部纳入男众的安排之下。这从佛陀本不许女性出家的观点上看,是有理由的;若从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看,似乎是相违背的,因为那等于是否定了女性的独立人格。如果此乃佛在世时即盛行于僧团的规制,那佛在世时的尼僧中,也不可能产生如此众多的成就非凡的圣比丘尼了。而佛教历史的事实是,部派佛教之后的佛教发展史,特别是佛教思想史上,有着许多的伟大的比丘罗汉及比丘菩萨,但很少见到比丘尼的记载了,尤其是在佛教思想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开拓上,尼众的功绩更是出奇的难得一见。
对于“八敬法”是否尚需坚持的问题,笔者认为当应慎重考量,须在充分讨论争辩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之后再予决定。但涉及女性与佛教之关系的问题,必须提到思想史的高度,进行认真全面的讨论,以澄清事实,厘清佛陀就此问题的教诲的历史背景及当时的现实因缘。佛陀的教诲,在许多涉及修学戒行、僧团规范的具体举措问题上,是十分注重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社会背景的。无疑的,佛陀以自身制定戒行和僧团规制的实践,揭示了一切诸法在因缘中流转、不可逆缘而为的真理。无怪乎佛陀一再告诫“小小戒可舍”,一再叮咛众生要“随缘”而“不变”。问题的症结在于,需要“随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似乎后来者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倾向,导致了佛教发展史上的众说纷纭、众彩纷呈的景观。
了解印度历史和现状的人们都十分清楚,印度社会不仅存在独一无二的“种姓制度”,而且也存在着十分严重的性别歧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一直是其主要社会矛盾之一。佛陀的时代更是如此。佛陀所开创的僧团,在组织形式和修学方式、生活模式上,与印度传统的“沙门”有着密切的承续关系,这是一个纯粹的男性世界。在佛教尚在北印度地区兴起之际,弱小的佛教沙门僧团如果接受女性出家为僧,进入僧团,将会在传统而保守的印度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如果一意孤行,不顾及印度社会的时机因缘,接受女性进入僧团,则那弱小的佛教僧团就必将遭遇一叶扁舟航行于波涛汹涌的汪洋之中的命运,其被淹没或掀翻的结局是没有悬念的。众人都清楚地知道,佛教在印度,到了十三世纪后就基本消亡了。固然其中有很多原因,笔者在专文中有论述,此不予赘述,但有一条是明确的,佛教在“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社会,倡导众生平等的观念,矛头直指“种姓”隔阂,是其最终被印度社会边缘化的主要原因。由此,我们能够理解佛陀当年接受大爱道女出家时的那份顾虑了,也能理解佛陀及以后的僧团始终将女性僧团置于男性僧团的从属地位的一番良苦用心和无奈了。也许,这就是女性僧团与男性僧团形成师生关系,以至于后世佛教称呼尼众僧团为“二部僧”之渊源。不同的时机因缘造就不同的僧团建制,对此,我们当能理解佛陀对男女平等观念的肯定,也能理解佛陀对社会因素、时机因缘的随顺善巧!
当今时代,女性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为此,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也应当顺应时代,作出切实的随缘转化。笔者相信,佛教界的大德们当能如佛陀那样,在当今时代因缘中,适应社会伦理的变化,顺应时代道德风尚的进步,对二十一世纪的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作出适当、恰如其分的调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