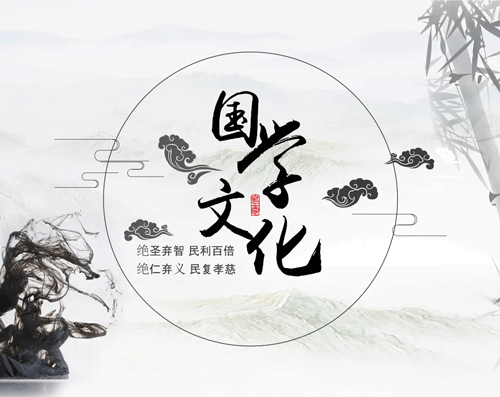略谈“格义”
发布时间:2023-09-19 12:04:55作者:互动金刚略谈“格义”
(韩廷杰(杭州))

一般来说,中国的佛经翻译分为三个时期:鸠摩罗什以前称为古译,罗什以后至唐玄奘时代称为旧译,玄奘法师以后称为新译。“格义”出现于古译时期。
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主要在民间进行,还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主要靠富人赞助。如竺法护翻译《正法华经》的时候,得到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续文承、赵叔初、张文龙、陈长玄的赞助。支谶翻译《道行经》的时候,得到孙和、周提立的赞助。此时的佛经翻译,纯属个人行为,没有梵本作底本,全靠印度僧人背诵,由另一个人译为汉语,称为度语。收另一个人记录下来,称为笔受,最后再进行修饰,《阿含口解》即属此类。
此时的译经,没有任何规划,印度僧人能背多少就译多少,迂残出残,迂全出全。印僧很难把大部头佛经全部背下来,只能背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此时的译经多为长经的节译本,如安世高翻译的《百六十品经》选自《增一阿含》,《十报经》选自《长阿含》,《八正道经》选自《杂阿含》,《本相猗致经》选自《中阿含》。
此时的译语还未成熟,如将佛陀译为浮屠,将沙门译为桑门,将维摩诘译为无垢称,将“如是我闻”译为“闻如是”等。
因为当时的译经师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深信歪曲佛法要下地狱,所以此时的译经方式都采取很拘谨的直译方式,音译也很多。使人很难看懂,所以三国时的支谦和康僧会主张尽量采取意译,尽量减少音译,还主张对译文加以修饰,使文字漂亮一些。此时又产生另一种倾向,删减太多,不能把经文内容完整地表达出来,竺法护又予纠正。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刚传入中国时,中国人很难理解。为了让中国人理解佛教,为了适应中国情况,译经师往往用中国原有的名词概念比附佛教,这就是“格义”。《出三藏记集》卷一,长安叡法师著《喻疑》称:“汉末魏初,广陵、彭城二相出家,并能任持大照,寻味之贤,始有讲次。而恢之以格义,迂之以配说。”可见格义起源于汉末魏初。
译经师唯恐中国人看不懂,边译边注,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即属此类。安世高翻译的《阴持入经》用“无为”比附“泥曰”(涅槃),《分别善恶所起经》所说的“笃信守一”很像是《老子》的“圣人抱一”。支娄迦谶和支谦都把《般若经》中的《真如品》译为《本无品》,显然是迎合老庄哲学的“以无为本”思想。支娄迦谶翻译的《般若道行经》,支谦重译时改名为《大明度无极经》,把“般若”改为“明”,也是迎用了道家术语。
竺法雅是格义的代表人物,《高僧传》卷四本传说他“少善外学,长通佛义。”这就为其格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又说“时依雅门徒,并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及毗浮、昙相等,以辩格义,以训门徒。雅风彩洒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与道安、法汰,每披释凑疑经要。”
此中“事数”即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带数释复合词。众本段引文可以看出,当时使用“格义”的,除法雅以外,还有法朗、毗浮、昙相、道安、法汰等,他们用“格义”方法教育自己的学生。除教内法师以外,使用“格义”的还有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他们的生活年代是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因为对政局不满,隐居竹林,清谈玄学,特别探求道家的“无”,以老庄理论接纳佛教。
当时有些高僧已经认识到,这种办法难以表达佛教真义,很容易歪曲佛教义理,如《出三藏记集》卷八僧叡着《毗摩罗诘提经疏序》称:“自慧风东扇,法言流咏已来,虽曰讲肆格义,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此中谈“六家”,即东晋时期专讲般若学说的六大家:本无宗、即色宗、心无宗、识含宗、幻化宗、缘会宗。说明东晋时的七宗,已经认识到“格义”方式容易损伤佛教本义,所以说法时不采纳这种方式。
道安、支遁等曾利用“庄老三玄”等词句解佛教义理,后来发现这种方法难以表达佛教本义。道安与僧光在飞龙山的一段对话,表达他对“格义”的看法。“安曰:先旧格义,于理多违。光曰:且当分析逍遥,何容是非先达?安曰: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竟鸣,何先何后。”道安已经认识到“格义”的危害,但他并没有彻底废除“格义”,当他教育弟子时,只许慧远使用“格义”。因为慧远既通“内学”,又善老庄。他利用《庄子》的话解释佛教的“实相义”。真正废除“格义”的是鸠摩罗什。
北魏时期(386-534)的昙靖和尚伪造了一部《提谓波利经》,《出三藏记集》卷五《新集疑经伪撰杂录》记载如下:“《提谓波利经》二卷,旧别有《提谓经》一卷。右一部,宋孝武帝时,北国比丘昙靖撰。”(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5页)此中“宋孝武帝时”即454-464年。
该经已佚,诸书引用甚多,从中可窥其大意。佛成道后去鹿野苑,途中为提谓、波利等五百商人讲五戒、十善等。在此继续利用“格义”,杂有中国五行说,并用五常比附五戒。天台宗创始人智顗(538-597)继承《提谓波利经》的传统,再次利用“格义”,其著作《仁王护国般若经疏》卷二称:“提谓波利等问佛,何不为我说四大戒?佛答:五者天下之大数,在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脏,在阴阳为五行,在王为五帝,在世为五德,在色为五色,在法为五戒。以不杀配东方,东方是木,木主于仁,仁以养生为义;不盗配北方,北方是水,水主于智,智者不盗为义;不邪淫配西方,西方是金,金主于义,有义者不邪淫;不饮酒配南方,南方是火,火主于礼,礼防于失也;以不妄语配中央,中央是土,土主于信,妄语之人乖角两头,不契中正,中正以不偏乖为义也。”智顗在此用五星、五岳、五脏、五行、五帝、五德、五色、五常配五戒,显然是利用了“格义”。
应当承认,“格义”这种译经方式,在佛教初传中国时,对于弘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仔细推敲起来,又不确切。直至今天,某些法师在通俗弘法时,也在利用“格义”,这只能使居士们了解佛法的大概含义。对于有相当佛学基础的居士弘法,应当使用纯粹的佛教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弘扬正信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