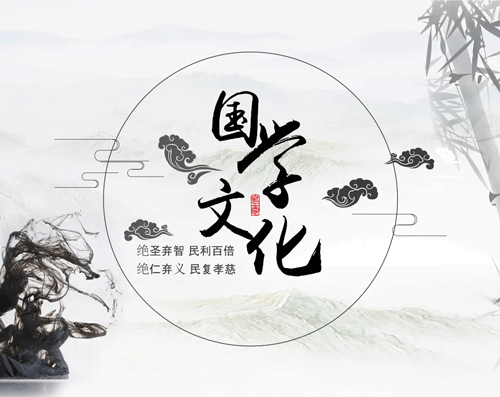佛教人生观
发布时间:2023-11-30 11:34:54作者:互动金刚
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何在?什么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对此类问题的解答,谓之人生观。只要是个智力成熟、精神正常的人,便不会没有他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人对自己存在理性审察的结果,持有人生观,可谓人这个被亚里斯多德称为“理性生物”的东西,与低一等的畜类之重要区别所在。愈是智力发达的人,愈是严肃认真地审视反思人生,确立自以为是的人生观。柏拉图说过:
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
只有精神不健全的人,才会不思考人生而象猪犬一样浑浑噩噩地活着。
人生观是人生旅程中的能源和方向盘,乃人全部生命的支柱。人生观的正邪、高下,决定着一个人行为的邪正、品格的高卑,生命的价值。确立正确的人生观,是做人的第一人事,先儒所谓“立乎其大本”者。
然而,正确人生观的建立,殊非易事。只要审察一下人生观所回答的问题,便不难发现它牵涉面极广,内涵极深:它关涉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宇宙万物的本质、人的本性及潜能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早就被人类科学文化列为根本课题,孜孜探究了数千年之久,直到今日,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全部成果,恐怕也未必能给出圆满答案,人生观问题,当然也就难以由科学知识提供具权威性、客观真理性的定论。
几千年来,东西方无数哲人俯仰低回,内省外照,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观体系,或悲观或乐天,或达观或淑世,或崇天命或重力行,或主禁欲或倡纵欲,或将人安身立命之本仰托于神谕,或将人生观的依据置于某种瑜伽的体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不论依何种人生观生活,大概都难以消除某些人生的困惑,或难以避免某种弊端。时至今日,科学虽然高度发达,人生观却大有衰退萎缩之势。在发达国家中,受流行思潮浸润的芸芸众生,不是在那种为古代哲人鄙弃的纵欲主义、消费主义人生观引诱下,拚命逐物,一任灵魂被腐蚀糜烂,行径沦于畜类,便是在信仰崩溃、自我丧失的困惑下,因找不到正确的人生归途而苦闷彷徨。流风所向,全球披靡。可以说,在人欲横流、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人类最为匮乏的,不是自然界的能源,而是精神能源——一种正确的人生观。
和许多古代哲学一样,佛教也把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列为人生之首务与大本。佛法四圣谛中第一苦谛,便专门回答人生观问题,就广义言,四圣谛中的集、灭、道三谛,及三法印、一实相印等佛学基本原理,戒定慧三学及菩萨行六度,皆是关于人生观问题的答案。小乘修行道的八正道,以正见为首,大乘菩萨行六度,前五度皆以般若为导,正见与般若的首要内容,便是正确的人生观和正确生活的智慧。
由于佛教对人生观问题极度重视,全力解决,更由于佛教圣者在古代东方特有的禅观中观察宇宙人生,以禅的高度冷静清澈的心境,及在禅定中开发的超常智慧,从全宇宙的广大视角和人自性最深潜能的层次上观照宇宙人生,使他们得以超越人类理性认识的局限,乃至超越科学的知识框架,直窥宇宙人生的真面,在如实正觉宇宙人生实相的深广智慧上,建立起圆满究竟的正觉人生观。这种正觉人生观,不仅是佛教徒所必须思察认同,而且对处于人生歧路徘徊中的现代人来说,提供了一种值得瞩目的人生观参照体系,是步入人类文化公园时不可不光顾欣赏的奇异景致。
佛教的正觉人生观,大略可分为两大方面。
立身处世,应先如实认识自己,明白人是怎样一种存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何在。这须对人的心理结构及从人类全部文化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性拓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人生是什么?从佛法看,人生是五蕴和合、因果相续的生命流转过程中的一个段落。五蕴者:一色蕴,主要指物质身体,这是一种生物性、动物性的生命活动过程;二受蕴(感受)、三想蕴(感知觉)、四行蕴(思维、意志等)、五识蕴(心识基本功能),为心理、精神活动。受想行识四蕴,高等动物亦未尝不具,只是不及人类发达,唯想行识三蕴中所具自我意识和理性认识的能力,被认为人所独具,乃人兽之间的基本分界线。
作为一种五蕴和合或灵肉结合的“萨埵”(梵语sattva,意为有情、众生),贪生畏死,避苦趋乐,大概可谓人乃至动物普遍所具的最根本特性。质言之,属于有情类的人,以有情识故,有好生、求乐的本性。不承认这一点,起码难以回答为何不自杀、不自找苦吃的诘难。自我意识明晰、理智发达的人类,其好生、求乐的需求,较之动物,内容至为丰富、深细。就求乐而言,人大概以需要满足而获得心理、精神上的适意感受为乐,或曰幸福。人的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除马斯洛所说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四层基本需要和高级的自我实现需要外,还可举出求知的需要、求自由的需要等,这些需要满足则得快乐,不得满足则感匮乏不安。愈为低层次的需要,其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愈是粗浅短暂,愈为高层次的需要,其满足所带来的快乐愈为深细持久。人品高低,大略依其所追求的需要满足之层次高低而定。
不论哪种需要之满足,总是以生——活着,为根本基础。一旦生命结束,便意味着快乐或幸福之终结,死,于是便成为对人生幸福的最大威胁。因此,自古以来,人类便有战胜死亡或永生的需求,这种需要常由宗教给予满足。秦皇汉武、历代道教徒之企求长生不死,神教徒之向往死后灵魂升入天国安享“永恒净福”,佛教徒追求常乐我净之涅槃,都是人类这种本性中最深或最高需要的反映。
纵观人类文化发展之历史,可以发现:人类总体,以不断追求幸福为趋向。在文化创造者的生命力推动下,物质生活在不断提高,精神生活在不断丰富,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其旨归,无非在于提高人生幸福度,提高人类自由度,这种发展,直指向未来,趋向无限,表现出人类有一种追求无限觉知、无限自由、无限幸福的本性冲动,有一种从有限直趋无限的趋向。这种直趋无限的向上追求,在宗教宣扬的永生、永恒净福、涅槃中,起码作了理想化的、抒情式的表达。宗教信仰的存在,充分说明追求永生、永恒幸福,是人本性深层的需求。
然而,只要以稍为冷静的眼光审视人生现实,便不难发现,人的本性需求与现实存在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人不但不能永生,不得绝对自由,而且生命短暂,必死无疑,束缚障碍极多;人不但不能常乐,而且有种种痛苦。对这不容掩饰的现实之揭露和承认,数佛法四圣谛的苦圣谛说得最为系统深刻。苦,可谓一切宗教的母胎,尤为佛教的出发点。
佛典讲人生诸苦,有内外二苦、八苦、三苦等说。内外二苦者,如《大智度论》卷十九说外苦有二种:
一者王者、胜己、恶贼、狮子、虎狼、蛇等逼害,二者风雨寒热雷电霹雳等。
内苦亦二种:一身苦,指身体感觉的苦,多属生理性的;二心苦,指精神感受的苦,多属社会性的。外苦、身苦,实际亦为心苦,为一种心理、精神上不适意的觉受。诸苦常被归纳为八苦:
1、生苦。出生所受的苦。《法蕴足论》卷五说,有情生时,领纳摄受种种之身苦事、心苦事、身心苦事,身热恼、心热恼、身燃烧、心燃烧等苦事故,说生为苦。人大概不记得自己生有何苦,但试观婴儿堕地,报以哭声,即证明其所受必苦。降生之后,无力自立,诸事皆依怙父母,不得自在,寒热饥渴病痛,唯有哇哇一哭。不但自己苦,而且累及父母保姆等受尽养育之苦。出身、长相,身心素质、智商、所处时地环境等,由降生一事所决定者良多,不由自己选择,往往能决定终身命运。生来贫穷下贱,或盲聋痴哑,其苦尤剧。《金色王经》云:
何苦最为重?所谓贫穷苦。
2、老苦。衰老一事,尽人难免。白居易诗云:“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老之至矣,生命衰竭,筋力不济,发白面皱,齿落眼花,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生活难于自理,思想精神亦僵化衰退,自感为社会多余之人,晚景凄凉,有若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3、病苦。人身危脆,病魔易侵。终生无病之人,世间罕见,道教称为“人仙”。疾病无论大小,无不痛苦切身,不用说痼疾沉屙,长期卧床不起,即便是头痛牙痛等小病,也不好受,谚云:“牙痛不是病,痛来要人命。”不仅病人自苦,而且给亲人、看护者造成痛苦。即使治疗有方,也难免服药、手术、扎针、注射及卧床住院等痛苦。此苦乃人最易体验者,不用笔者饶舌。
4、死苦。死亡,不仅意味着人生幸福之终结,永诀所爱乐的亲人、事业、财产等一切,而且临死前多罹疾病,临终之际,据佛典言有如生龟脱壳之苦。死后神识有无及去向,未可卜知,前路黑黑,岂不哀哉!《瑜伽师地论》卷六一谓死苦有五相:
一离别所爱盛财宝故,二离别所爱盛朋友故,三离别所爱盛眷属故,四离别所爱盛自身故,五于命终时备受种种极重忧苦故。
5、爱别离苦。人是感情动物、社会动物,以亲友恩爱为维持生命之重要食粮。《大乘义章》卷八云:
依《涅槃》,以多恩义,故名为人。人中父子亲戚相怜,名多恩义。
亲人团聚则乐,离别则苦,然亲属朋友,生离死别,尽人难免。生别者,或为战争、事务所逼迫,或男女之间情感破裂,令人肝肠寸断,魂牵梦萦。死别之苦,更为深重。谚云:“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父母归天、爱侣亡故、儿女夭折、良友谢世,纵使铁石心肠,也不能不痛彻肝腑,苦泪涟涟!
6、怨憎会苦。所爱之人不得不离别,不爱之人,如怨家仇敌、盗贼恶棍、阴险小人、情敌、政敌、胜己者等,却不容回避,不得不生活于同一时空,乃至同一单位、家庭,受其扰害,使人或苦恼不安,或嫉恨不宁。
7、所求不得苦。人生莫不有种种需要、追求,然求之不得,乃属常事,诸事顺遂、终身幸运者,总不多见。考试落第、谋职不得、求爱遭拒、生意蚀本、企业破产、比赛失败、失业、失恋等,无不使人忧愁不安,烦闷不快,甚至因此而痛不欲生、自寻短见者,亦大有其人。
8、五阴炽盛苦。以上七苦,归根结蒂,皆为身心所受,亦终为身心的存在和活动所致,或者说身心的活动本身便是苦之渊薮。《杂阿含经》谓“于人世界中,有阴皆是苦”。尤其人之肉身,危脆不坚,污秽不净,绝非理想的生命形态。庄子《齐物论》反省人生之苦说: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然疲役而不知所归,可不哀邪!……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从来的哲人智土、英雄豪杰,面对死亡的悲剧,莫不感叹嘘唏,从而研讨抗拒死亡之道,柏拉图甚至称哲学为“研究死的学问”。美国心理学鼻祖威廉?詹姆斯称死为潜伏于人各种幸福欢乐的虚饰之后的“深藏的蛀虫”。德国人类学家舍勒(m.sheler)认为,所有的人,无论他承认与否,都必然对这“深藏的蛀虫”怀有某种确定的直觉。精神分析学家齐尔伯格认为,在人面对危险时的不安全感、懦弱和压抑感等后面,永远潜伏着对死亡的恐惧,其存在经得起严密推敲,没有谁的意识深层不藏有这种恐惧。存在主义者克尔恺郭尔、心理学家弗洛姆、人类学家奥托?兰克尔等,都认为死亡恐惧是普遍存在的,它决定了人的悖论本性和存在困境:人是生理性的肉体与自我意识(“符号性自我”)的矛盾对立统一体,这一悖论是人真正永恒的本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贝克尔(1924—1974)在其《对抗死亡》中力论:人的这种悖论存在,意味着人既是小小神祗,又是蛆虫口中食,既是具有神性的天使,又是排泄出臭秽之物、终归腐朽消失的兽类。如此痛苦的二元分裂,是人的精神所难以承受的。为了抗拒死亡,人们拚命创造各种文化,建设“神化工程”,以图从潜意识中抹去死亡的威胁和无力战胜死亡的事实。达观哲学、神教信仰、爱情、艺术、娱乐等,都具有弗洛伊德所说“移情”手段的性质,是转移死亡恐惧、对抗死亡的防御机制。实际上,对死亡之事实而言,它们终归不过是一种软弱的自我安慰、自我麻醉手段,具有精神鸦片的性质,不可能从客观上令人真正摆脱死亡结局,获得永生。这无疑是深彻人性之谈,与佛法的生死观颇多共同点。
的确,那种掩饰死亡痛苦的达观哲学,显然浪漫不实。如西哲伊壁鸠鲁说人未死时死尚未到,曷用怕死,及死到来时什么都不知道了,有何苦痛?若如其言,则一切大事,皆无须早作预备,而死时什么也不知道,纯属无根据之想象,经不起事实验证。如此对待死亡,实属自欺欺人。又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在教人注重现前生活,不必考虑力不可及的死亡之事,这也不过是无力战胜死亡的妥协之词。儒家面对死亡威胁,倡立德立言立行,以期身死而精神思想不死,较卑者则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虽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能否真的死而不亡,仍大可怀疑。思想、精神、德行、作品,纵使长留人间,亦须依别人、人间社会而存,而别人、人间社会乃至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乃至宇宙,皆为无常之物,皮若不存,毛将焉附?庄子谓人死“反入于几”,与“万物一府”,看来虽然达观,骨子里实掩藏着一种对人生无常的悲哀。至于常人出于种类延续的动物性欲望,将不死的需求寄托于子孙后代之繁衍不断者,更为愚痴。子孙后代,各有其独立人格,各有生死,纵使能延续万代,也丝毫不能说明自身战胜了死亡。
总之,无论怎样以达观哲学自慰,用移情手段遮掩,其实都是不敢正视死亡悲剧,不敢真正解决死亡问题以满足人本性求生求乐欲望的表现。对于人这种万物之灵而言,以如此态度对待人生根本问题,未免过于软弱卑怯,未免过于自轻自贱!
佛教的态度则与此颇为不同:首先敢于正视死等人生诸苦,毫不掩饰遮盖,而把人生缺陷与根本问题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认清其可悲,然后研求根本解决之道。
由佛法观,人生固然以死为最大痛苦,然死依生而有,有生必有死,欲解决死的问题,必先解决生的问题。生死,于是被佛法突出为人生的根本问题。强调“生死事大”,人本性中对涅槃的需求与现实生死之苦,乃佛法所揭示的人生根本矛盾或人存在的悖论。“了生死”,从而被佛法列为中心课题。此所谓“了”,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了彻,谓穷彻生死的因果、实质,掌握超生脱死之道;二是了结,谓永远结束、消灭生死之苦。
在佛陀慧眼观来,人生之悲剧,不仅在于现前八苦交攻,更在于死亡并非苦的终结,而是有死还必有生,死后必为生前所造业力所缚,轮转于六道中,永无止息,若再生于人中倒罢了,而人却极易堕入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失去了再做人的资格,其苦痛较之于人,更是不堪言喻。这种生死流转,是更大的苦。佛法因此决志了却生死流转,认为生死流转的根本问题不解决,其它一切随生死而有的诸苦,即使有可能通过移情手段减轻,终不可能消灭,生死不了,一切诸苦,会永远没完没了。反之,生死若了,则一切皆了。犹如伐毒树,若断其根,枝叶永尽,若不断根而唯在枝叶上砍削,旋砍旋生,永无除期。不把解决人生根本问题列为大课题,只知解决小问题、枝末问题以求妥协苟安,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小问题也未必能解决得好。
若就人生之全面而言,佛法亦不否认人生有乐,说人生基本上是苦乐间半。无容否认,人有极为丰富的乐趣:有饮食男女之乐、天伦之乐、情爱之乐、友情之乐、游戏娱乐之乐、工作劳动之乐、艺术欣赏及艺术创作之乐、事业成功之乐、求知学习之乐、道德修养之乐……,其乐之丰富深细,远非动物可及。但佛法认为这些乐无不依一定的条件而生,《瑜伽师地论》卷五名之为“非圣财所生乐”,说非圣财所生乐须依适悦、滋长、清净、任持四种资具而生。既依缘生,则其乐必然相对、有限,“不遍所依”、“受用时有边有尽”,容易“为他劫夺”。
苦乐在生活中所占比重,因人因时地而异,据心理学家福楼格勒(flugel)研究,当代西方人平均一生喜乐占50%,痛苦占22%,不苦不乐占28%。有的人苦要多得多,但苦纵极多,也总还有乐。
佛学认为,若作深一层观察,则非圣财所生乐,亦以苦为实质。何以故?一切乐受皆依缘生,皆无常变灭不可常住,与人常乐的本性需求相违故,此乐之当体,即是“行苦”。《杂阿含》卷十六第437经载佛言:
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行变易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
诸受皆苦,被列为小乘四法印之首。无常故苦,乃佛法苦谛之根本义趣。《长阿含·大本缘经》佛言:
因乐触故生乐受,若乐触灭,受亦俱灭。
乐缘既灭,乐亦随灭,必生“坏苦”。世间之乐,莫不如此,没有不散的宴席,席散人空,乐极生悲,倍感凄凉。而且,就整个人生而言,有谁无苦?苦乐如形影不离,如《大般涅槃经》卷十三所言:
生死之中,实有乐受,菩萨摩诃萨以苦乐性不相舍离,是故说言一切皆苦。
依佛法真谛,人生之苦,更在于无我。所谓乐,以能受乐的主体自我为本。人所认为的自我,无非我的身心、社会身份、个性等,由满足此“我”之需要,乃生乐受。如饥渴时得甘美饮食,便觉爽快,寂寞时遇知音,便觉悦愉。然此所认能受乐之我,乃五蕴和集,假名为我,而念念变易无常,无一常住真我实受苦乐。能受乐的主体既如此,所受之乐亦如是,亦无常变灭,不属我有,非即是我。《长阿含·大本缘经》佛说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受,皆“有为无常,从因缘生,尽法灭法,为朽坏法,彼非我有,我非彼有”,又云:
若乐受是我者,乐受灭时,则有二我,此则为过。
苦受亦如是,念念灭故,非常住真我。无论苦乐,皆非我而属因缘故,不得自在真常,故实质是苦。《大般涅槃经·一切大众问品》谓“一切属他,则名为苦”。
佛法盛谈人生诸苦,唱“有生皆苦”,乃至说乐亦是苦,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否定人生价值、悲观厌世之嫌。未能吃透佛法真精神的西哲尼采,取佛法糟粕,说人最好快点死去,以离开痛苦的尘世而归于寂灭,这实在是对佛法的片面曲解,正是佛所谓“饮乳成毒”者。实则佛法力说苦,只是针对世俗文化掩饰人生缺陷的破执之谈,旨在发聩震聋,唤起世人对人生现实、人生根本问题的正视,有了正视,才谈得上解决。
佛法认为,苦,仅是对迷昧人生而言,若觉知是苦,深观诸苦而发起超出生死的“出离心”,则人生诸苦,未必不是一件幸运事。若无苦纯乐,一如诸天,人便难以发起出离心;若众生无苦,则菩萨难以兴慈运悲而发尽度众生皆共成佛的菩提心。《起世经》中佛言:有三天使住于世间:老、病,死,它们应看做天神为警策世人发心求道、升华生命而派来的使者,应奉为师长。就此而言,人生诸苦,只要换一个正觉态度,便变成了珍贵之物,成为培养菩提觉花的肥料。对真正学佛者来说,人生无苦,反为缺憾。元代妙叶大师“十大碍行”谓“念身不求无病,身无病则贪欲乃生,贪欲生必破戒败道”;“处世不求无难,世无难则骄奢必起”;以病苦为良药,以患难为解脱,才是佛弟子对待苦难的精神。日本学者木村泰贤《大乘佛教思想论》说:
苦对于我们成为征服的对象时,便发挥其伟大的道德价值。反之,任己被苦征服,人生便可谓无价值的存在,这即是佛教的根本精神。
当然,欲征服苦,必先承认、正视苦,若连承认都不敢,谈何征服?
而且,佛法说苦,乃证得涅槃之乐的圣者从其大悲心中观照世人而说,言人生苦,是与涅槃真常之乐相比较而言。何况说苦,只是佛法世俗谛之一面,若从另一面真实谛观,苦生灭无常、无自实体故,当体是空。《摩诃般若经》卷一谓“知苦不生,是名苦谛”。知无苦可灭,才是苦谛的究竟实义。
真正学佛人,纵然身受众苦,乃至为济度众生而主动受苦,因证得苦性本空故,亦甘之如饴,不改其常乐。纵死期到来,因自见去处故,亦视死如归,毫无畏惧。这较世间英雄豪杰之壮烈而死,更为洒脱自在。
佛法关于人生价值评判的另一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面,是充分肯定人生的优胜,重视人应有的价值和尊严,教导人充分发挥自己特性,开发自性潜能,创造最高的人生价值。
从佛法观来,现时地球人虽然寿命短促,苦乐间半,但较之寿命甚长、多乐少苦乃至纯乐无苦的天道众生和其它星球上的人来说,具有极为珍贵的优胜之处。《长阿含》卷二十载佛言,阎浮提(地球)人有三事胜余三洲(外星)、鬼道及欲界天:
一者勇猛强记,能造业行;二者勇猛强记,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强记,佛出其土。
《大毗婆沙论》谓“人”有三意:“一止息,二忍,三末奴沙(于工巧业处得善巧)。”又有八义名为人:聪明、业果胜、意细微、能正觉、智慧增上、能别虚实、圣智正器、聪明业所生。太虚大师说:
人之特性,具有造作、思想、觉悟之自由活动的能力。
总括诸说,佛法所肯定的人道优胜,大略有三个重要方面:
1、聪明善思,富创造性。
与动物相比,人的感知器官最为全面发达,尤其意识最为发达,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和悟性,此即《大毗婆沙论》所谓聪明、意细微。《俱舍论疏》谓“多思虑故名之为人”。思维能力发达,心灵手巧,使人具有很强的创造能力,能不断增长知识,提高智能,创造出自己特有的科学文化。在物质方面,人穷研器用,精思入神,发明种种机械,掌握种种技术,用自己创造的物质成果严饰自身,便利生活,不断提高在物质世界中的自由程度,庄严世界,令星球改观,山河增色。时至今日,人类已乘飞船遨游太空,令神话变为现实,充分表现出《毗婆沙论》所谓“于工巧业处得善巧义”的特性。在精神方面,人利用文化符号,创造出哲学、文学、艺术等辉煌成果,如百花竞放,景象日新。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世界是人以其聪明才智创造的文化成果。人的这种创造能力,不但动物难以相俦,即诸天鬼神,恐怕也要惊奇称叹。
2、 自宰自制,自由塑造。
《大毗婆沙论》卷一七二谓人有“止息”义,并云:
能寂静意故名人,以五趣中能寂静意无如人者。
止息、寂静意,谓具很强的自我调控心意、宰制行为的能力,能止息意马心猿的驰骛而令心意寂静,不仅能按道德规范约束行为,而且能控制本能欲望,摒绝声色犬马的诱引,修清净离欲的“梵行”,乃至以瑜伽禅定自净其心,自究其心,进行生命的自我变革,超出生死。止息、寂静意或加忍,意味着人有很强的意志力,能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克服内外障难,忍受困苦凌辱,表现出勇猛精进、坚韧不屈、百折不回的毅力、忍力。
人的这种特性,使人具有高度的意志自由和自主性,具有很强的自塑能力,能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乃至超凡入圣,成就佛果。人的自塑能力,近今西方人类学也给予很高评价。m?舍勒《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认为,“人是—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这不仅在于人有理性与工巧技术,更在于人有超越自身的意向性和趋向。人,是两个生命之流中的中介、过渡,一个永恒超越自身生命的向前流动。生物人类学家阿尔诺德·格伦等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未特定化”——人实际上是一种未完成、未确定的生物,或者说不同于动物之出生即完成确定,人是在出胎后才逐渐完成、确定的。正因为人具未完成性,故能不断寻找存在方式,解决自己的存在难题,解释、确定、完备、发展自己。这与佛法所说人的特性可谓不谋而合。
人具有自由塑造之能故,使人可以自由选择人生道路,创造生命价值,不仅可自由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自造前程,而且可众人合力,共造共同使用的“依报”——国土世界。佛法高唱“万法唯心造”,说众生所受用的根身世界,终归为自心所造,由心起念,由念起业,业力感召,能变造根身器界。变造的可能性,依天台宗一心十法界义,起码有十大层次:天、人、阿修罗、鬼、畜、地狱六凡法界,加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每一重法界各具五蕴(正报)、众生、国土三种世间,十法界互具,凡三千世间,此三千在我人当下一念中圆具,《摩诃止观》卷一云:
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百法界;一界具三十种世间,百法界即具三千种世间。此三千在一念心。若无心而已,介尔有心,即具三千。
一念三千,意味人之一心,理具或体具宇宙一切,具有变造一切形式存在的可能性、自由性和本钱。变造之机,唯在心念。若心随染缘,迷心逐物,造十恶五逆之业,便造就地狱、饿鬼、畜生法界;若心随净缘,修心修善,修定修慧,可造就贤人圣哲,由人而天,乃至由人而罗汉、缘觉、菩萨、佛。或沉或升,或堕世间或出世间,唯在如何运用自己心财进行变造,不由天命,不由神意,不由他人,唯由自己,唯由自心,所谓自作自受,不由于他。这是人最极宝贵的特性。
人皆具此特性故,虽同为人类,因用心不同,所造千差万别,使人间呈现出一派十界咸备、善恶悬殊、人格形象各异的纷纭景象:有人凶残狠毒,害人祸众,过于毒虫猛兽;有人荒淫无耻,伤风败俗,被目为衣冠禽兽;有人蝇营狗苟,丧失人格,寄生偷生;有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成为公害;有人则倾心尽力,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为国为民,乃至粉身碎骨,牺牲自己,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求进步,表现出菩萨风范;有人则精勤求道,勤修苦炼,或开发异能而被目为神仙,或清净六根而成罗汉;有人更圆满觉悟,成为大觉佛陀,为人天师表,万世楷模。这可谓人道的突出特色。
人因生命力、创造力强大故,向上与向下的造诣,都可至于极限。若论向下,则人要堕落起来,丧尽天良,灭绝人性,共用心之险恶,杀害之残酷,远过凶禽猛兽。人要是贪淫起来,纵欲无度,种种性变态,真是猪狗不如。人要是私欲膨胀,欲壑无底,如帝王野心家,恨不得将整个世界霸为已有,国土跨洲,财宝山积,后妃千万,奴仆无数,犹想夸张;豪富巨贾,资财亿万而敲剥益酷。若论向上,则人能慈及万类,惠及百世,智烛千古。仁人志士杀身成仁,菩萨行者济人救世,其心地光明,可上格日月,人格高尚,可令天地惊、鬼神泣。不论向上或向下,同是一心之用,不出一念之差。人之初生,恰似一块泥团,有人用它自塑成英雄豪杰、庄严佛像,有人却用它自塑成权奸巨蠹、暴徒恶棍。
更要者,在由佛法观来,不仅个人起心造业,可自塑此生的人格形象,而且决定他生后世乃至多生多世的流转升沉,若放逸散漫,行恶造罪,将堕入三恶道,长劫难出,后悔莫及。短短几十年,却造成决定未来升沉的业行。每人的业行,还会辐射于社会和自然界,影响及于子孙后代。人生者,确实重要至极,岂可轻忽而过。
3、 善能自觉,最为佛种。
大乘佛法高唱众生皆有佛性,凡有心者皆定当得无上菩提。此所谓有佛性,谓具有成佛的可能性和本性,有如矿中藏金。又谓众生心识体性本寂、本净、本觉,本来不生不灭,本来是佛,只不过迷昧不觉而已。当然,现实成佛,须资仗因缘。成佛之因,即自觉发菩提心,立誓上成佛道、下度众生,以圆满正觉为最高理想。
发菩提心,本身须有出离生死的迫切需要,须对众生生死流转之苦具深切感受与同情,此唯苦乐间半、八苦交攻而又最具觉性、意志、同情心的人类,才最易发起。佛典屡言,鬼、狱二道众生被众苦逼迫,无暇发菩提心,畜道众生愚痴故不可能发菩提心,天道众生贪着乐受、无苦恼逼迫故,不易发菩提心,唯人最易发心求道,故佛言:“人间于天则是善处。”1。
成佛之缘,除众生苦等外缘外,最重要者,是有佛出兴于世,高擎智灯,为人师表。而佛之出兴,皆在人间。《增一阿含·等见品》佛言:
诸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
佛陀自称:“我身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成佛。”天帝供食,问佛陀用天食抑人间食,佛言:“用人间之食。”并说“我亦在人数。”表示对人间的珍视和肯定。佛法以人间为修道成佛的最佳道场,“四十华严”卷十二云:
人是福田,能生一切诸善果故。
谓三乘贤圣道果,皆“依于人而能修证。”何以故?人间多苦多障难,而人身能思能觉,最具造诸善功德的条件;人间多贫穷困苦、多愚痴邪见故,正好修财法二施,积集福德,广结人缘;人间多障碍魔难、怨嗔憎嫉故,正好修持忍度,锻炼毅力、忍力;人生苦短,时光催人故,正好修持精进度,精勤不懈;人间多学说义理故,正好修持般若度,获得妙观察智;人间多所缺憾而人类又具向上趋求故,正好以人间文明的建设为菩提道,万善齐修,净化社会,利乐众生,庄严国土,弘宣正法。就此而言,人乃上好福田、上好智田,最宜播菩提种,育般若苗,结大觉果,不仅优于诸天,甚至比诸佛净土还要优胜。《无量寿经》即载佛言:
汝等于是广植德本,布恩,施惠,勿犯道禁,忍辱精进,一心智慧,转相教化,为德立善,正心正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
佛陀以洞彻众生自性最深潜能的慧眼,见人人皆具佛性,本来是佛,与佛平等不异,对人的尊严和应有价值,给予最高的肯定,给人展示了圆满自我实现的终极人生图景,予人以巨大鼓舞激励。
佛法认为:个人作为独立经验单元,有其不可抹杀的权利与价值,有权自我解脱,许人先度自身,“别别解脱”,独自出离生死。佛法更认为,众生互相缘起而存在,互相之间皆有深恩,应视同父母眷属。彻底的出离生死,应该是普度众生同趋觉路,大乘甚至斥不愿度众生的自了汉为“焦芽败种”。
因为人具诸优胜,最为佛种,人生乃升沉凡圣之关键,故佛法对人生极为珍视。佛经中常感叹“人身难得,诸根难具,佛法难闻,明师难遇”,教人珍惜人生,珍重佛法,以正法为导而善度人生,善用人生,创造应有的人生价值。依佛*轮回业报说,具有持五戒不犯的福德,才能直接生于人间。至于值遇佛法,须宿世与佛有缘。而人中能严持五戒者不多,故多数人百年之后,再生人间甚难,佛经中常喻为盲龟于大海中值遇一有孔可以附载的浮木。佛陀曾用指甲从地上挑起一点土,问弟子佛指甲上土多,抑大地土多,弟子当然答:大地之土比于世尊指甲上土,其数之多,不可称量。佛言:人命终后,生于三恶道中者,多如大地土,生于人中者,少如佛指甲上土,天中命终者亦如是。一堕入恶道,再复人身,历时甚久,而且即使再生人中,前世记忆尽失,一切皆须从头学起,值遇佛法而有因缘起信发心,更为难得。
据佛典之说,在长劫轮回中,佛法住世时间甚短,犹如电光一闪,如难得一开、开后即萎的优昙花。释迦佛出世,正法时期,我等既已错过,幸法、僧二宝尚在,有缘遭逢,良机万劫难得,岂可白白错过,应依佛教诫,精进修持。《法句经》偈云:
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
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从来高僧大德,为自度度人,精进不已,惜时如金,昼夜勤修,一分一秒都不肯白耗虚度,心心念念都求与般若相应,表现出极度珍惜人生的精神。这与那些在麻将桌上、扑克牌中、鸟笼子前消磨时光的庸人,那些夙思夜梦营私利、费尽心机谋算他人的恶人,其人生态度,人生价值,形成鲜明对照。若论珍惜人生,积极向上,可谓至佛法而达极限,谤佛法人生观为消极,显然是颠倒黑白。
佛法虽教人观世间苦,发出离心,菩提心,以了生死为终极理想,但并不主张逃世避世,为他生后世的解脱(《杂阿含经》称“非时乐”)而牺牲现世的利益,忽视人间的建设。佛法的根本精神,是以解决人生根本问题为本,将发达现实人生与超生死出世间的大事结合为一体,教人树立正确人生观,依正见生活,以净心从事世间事业,即人间建设而双修福慧,令社会净化,国土庄严,世界和平。佛法诸乘修持道,都依此精神而制定
大体而言,佛法菩提道,可分五乘渐道与一乘顿道两途。五乘渐道者,以人天乘法为基址,教人先正信因果,具三归,持五戒,行十善,敦伦尽分,尽职尽责,习技艺,如法求财、理财,交善友,慎出纳,具《长阿含经 善生经》所言方便、守护、善知识、正命四种具足,在家庭和社会中做一个好人,过好物质、伦理和精神生活,得“现法安乐”。太虚大师《佛陀学纲》说得好:
学佛的第一步,在首先完成人格,好生地做一个人……完善物质的生活,增高知识的生活,完善道德的生活,再以此完成优美家庭、良善社会、和乐国家、安宁世界。

乃至成就人中圣人,在此基础上,发出离心、菩提心,修三学六度。这并非应机应时的方便之说,而是从《阿含经》到大乘经中所表述的如来说法之本怀。阿底峡大师曾将这种渐道总结为从下士道入中士道、中士道入上士道的“三士道”。
一乘顿道者,即以五乘佛法、世出世间为—,以人间社会为道场,以出世间的无我心、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大雄猛心,在服务社会、利益民众的世间事业中去修菩萨六度万行,在济世度人的活动中完善人格、圆满福智,并利乐有情,庄严国土,带动众生一起同趋涅槃之域。
无论渐道顿道,莫非以发达人生、圆满人生为本质。人若能以佛法正见为导而过正觉生活,力行众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则必然能使人格日渐完美,智慧日渐增长,家庭社会关系日渐和谐,对社会的有益贡献日渐增加,生活日感幸福,获得“现法安乐”及“圣财所生乐”——所谓圣财者,有七种:一信(对佛法的确信)、二戒、三惭、四愧、五闻(听闻正法)、六舍(舍恶、舍财等布施)、七慧。这七圣财所生乐,不同于世俗的非圣财所生乐无常难保,而具能“起妙行”、“乐广大遍满所依”、“一切时有”、“受同时转更充盛增长广大”、“无能侵夺”、“可从今世持往后世”、“无怖畏”、“无怨对”、“无灾横”、“无烧恼”、“能断后世大苦”等殊胜,可谓真正的利乐,得此利乐,则人生不谓之苦。若更精进修持,明心见性,证入圣果位,则得真常乐,真正根除生死怖畏。或深心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生永出生死,将来回入此界度化众生,则其人生价值,更可称叹。如此人生,才可谓真正的人生,应有的人生,如此度过一生,才可谓不枉此生,不愧此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增一阿含·等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