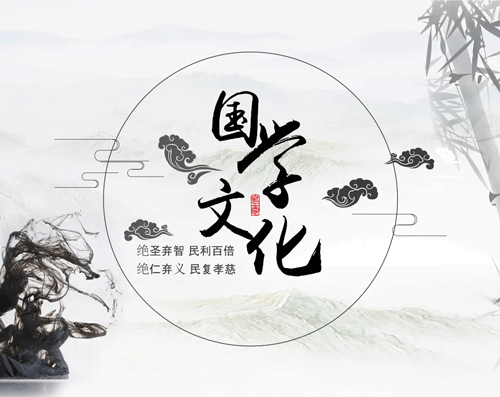法眼文益《宗门十规论》禅法思想及其价值辨析
发布时间:2023-11-05 13:33:37作者:互动金刚一、 文益与《十规论》
文益(885—958),俗姓鲁,余杭(属今浙江杭州市)人。文益年满7岁时,遂到新定(治所今浙江淳安县姜家镇东南)智通院,礼全伟禅师座下出家。年满20岁时,前往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开元寺求受具足戒。
文益受戒后,前往明州的育王寺(在今浙江鄞县),师从弘扬戒律的希觉律师学习律学,与此同时,也学习儒家经典。由于文益学习十分优秀,被希觉律师誉为“我门之子(子游)、夏(子夏)也”[11]。可见希觉律师对文益是十分器重的。但文益本人并未因此而感到满足,后来对禅宗发生兴趣,便离开育王寺南下,从福州长庆院慧棱禅师学习禅法,但没有得到证悟。
后来,文益与同修结伴,继续南下。至漳州(治所在今福建漳浦),见桂琛禅师(867—928),与桂琛问答之间,文益深深被桂琛的禅悟境界所感动,于是事师桂琛并得悟受法。
文益在桂琛处得悟受法后,先后住持临川(即抚州,治所在今江西抚州市西)崇寿院[12]、金陵报恩院[13]、清凉道场[14],深受南唐国主[15]及公卿[16]的礼遇和爱戴。于后周显德五年(958)示寂,享年74岁。南唐国主谥以大法眼禅师之号,又谥大智藏大导师[17]之号。后来李煜继位之后,又为文益立碑颂德,秘书监、兵部尚书韩载熙撰写塔铭[18]。由此可见,文益在当时及后来影响广大而深远。
《十规论》一卷,为文益所撰。文字简洁,语言精炼,思想扼要。有续藏经录本和天津刻经处刻本流通。但是,《十规论》自五代成书以来,流传并不广泛。从现成的文献记载来看,一直到400后的元代,才有少量的刻本流通。据元代无愠恕中禅师在《题重刊十规论后》[19]中记载,元至正六年(1346),有杭州府钱塘县南屏山佛慈法喜悦禅师将自己所藏《十规论》,让恕中在径山寂照院刻板印行。刻成后,因径山遭兵火,经板不存。后来有山西五台县台州的委羽旻上人捐资重刻。这是现存文献中知道刻本的最早记载。后来此论也一度传入朝鲜和日本,并在日本有过三次刊刻,[20]但其影响十分微弱。
此次对《十规论》禅法思想的考察及其价值的辨析,主要以续藏经录本为主,并以天津刻经处刻本为参考。
二、《十规论》的禅法思想辨析
中国禅宗之南宗禅法,自六祖慧能(638—713)以后,流传和影响甚广,历代授受,各得心要。至文益时期,已形成不同流派。文益自己在《十规论》中,将不同流派的禅法,归纳为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四种类型,对当时的禅法思想及禅风,一一加以评述。可以说,文益是对唐末五代的禅风作最后的整理和总结,在中国禅宗思想史上,具有特别而又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对《十规论》的研究和了解,可以为正确认识唐末五代时期禅宗内部禅法及禅风的不同面貌提供方便。
下面,我们仅对《十规论》中所反映出的文益的禅法思想分别加以介绍。
(一) 禅法参悟必须不失禅宗根本宗旨
中国的禅宗,特别是南宗的禅法,倡导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修证的纲领。南宗正因为是以“直指人心”为参悟方法,所以,从直指上来说,南宗禅法又被称为顿悟法门。后世的禅门巨匠,在禅法参悟的过程中,正是以“顿悟心地”为方法,“见性成佛”为目标,终身以此为修习禅法的根本宗旨,最后让自己的生命发生质的飞越,从而证悟人生的真谛。
禅法参悟的这一根本宗旨,到了文益所处的时代,有的禅法学人似乎已忘失而全无所知,以致形成懒于参求,徒具虚名的禅风。于是文益在《十规论》中指出,“论曰:心地法门者,参学之根本也”[21]。目的是提醒禅法学人,不应忘却参悟禅法是以“顿悟心地”为根本宗旨。文益同时还指出,如果参悟禅法离开了“顿悟心地”这一根本宗旨,而“但知急务住持,滥称知识”,是“全丧正因”的表现。其结果是“乍饮铜汁(地狱之报),大须战慄,无宜自安,谤大乘愆,非小果报”。目的是警诫禅法学人,参悟禅法如果不明心地,是十分危险的。不但很难摆脱地狱乃至六道生死的束缚,甚至还有诽谤大乘佛法的重罪。总的说来,如果参悟禅法不以“顿悟心地”为宗旨,对自己了生死的愿望是有害而无益的。
同时,对于“心地”的内涵,文益作了这样的界定,他在《十规论》中说:

心地者何耶?如来大觉性也。由无始来,一念颠倒,认物为己,贪欲
炽盛,流浪生死,觉照昏蒙,无明覆盖,业轮推转,不得自由,一失人身,
长劫难返。所以诸佛出世,方便多门……祖师哀悯,心印单传,俾不历堦
级,顿超凡圣,只令自悟,永断疑根。
在文益看来,所谓“心地”,就是一切众生内心本具的光明觉悟性能。但是,由于众生无始以来受无明的牵引,妄生我、我所(物)的执著,以我、我所为基础产生贪欲,因贪欲而造恶业,有恶业便会遭受痛苦的果报,而长时间不能远离轮回的束缚。正因为如此,诸佛以大悲出现于世,说法度生,因机施教,无数方便;历代祖师,弘宗演教,传佛心印。目的都是为让一切众生能认识并证悟自己内心本具的光明觉悟的性能,使之照破黑暗,摆脱生死,超凡入圣。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顿悟心地”成了生死轮回和超凡入圣的分水岭。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参悟禅法的过程中,文益是十分重视禅宗“顿悟心地”这一根本宗旨的。这也是文益禅法思想中最闪光的环节。
(二)参悟禅法必须与经教协调
佛法不同于普通学问,那就是佛法是十分重视宗教修证的。但一切众生在修证佛法的过程中,是需要掌握一定方法的。而这种修证方法的获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按照佛法的观念,有情众生无明的习惯势力很大,要想获得修证方法,必须依靠听闻记录佛陀说法的经教。因此,佛教自传入中国,进入南北朝以后,就出现如何处理修证与获得修证方法(听闻经教)关系协调的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国佛教发展到唐末五代时期,则形成以禅法修证来代表佛法修证的局面,这就是常说的“宗门”;与此相对应的重视经教研究的宗派则被称为“教门”。因此,早期佛法修证及如何获得佛法修证方法(听闻经教)的问题,就成为参悟禅法的“宗门”与重视经教研究的“教门”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必须明白的是,“宗门”与“教门”的关系,本是相辅相成的。参悟禅法必须以经教作为指导,而经教研究必须靠参悟禅法来实践。经教研究是参悟禅法的工具,参悟禅法是经教研究的验证。正如菩提达摩(?—536)在《二入四行论》中指出,参悟禅法必须“藉教悟宗”[22]。在菩提达磨看来,“悟宗”必须依靠“经教”。也就是说,要想领悟到佛法的真正宗旨,必须要依靠语言文字作为辅助力量。后世将语言文字这种辅助性作用,喻为是引导人们认识月亮的手指[23],把语言文字这种辅助性的作用说得更加形象。菩提达磨的这一主张,可以说是为以后参悟禅法与经教研究的关系如何协调指明了方向。而禅宗后来的学人,对参悟禅法与经教研究的关系的处理,有时是不恰当的,甚至有矛盾的倾向。
比如唐代中期,禅宗内部也面临这种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宗密大师(780—841)在其《禅源诸诠集都序》一书中,提出“禅教一致”等十条[24]来协调禅法修证与经教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处理不协调,对于整个修证佛法来说,都是极大的障碍。到了文益的时代,这一关系如何协调,仍然纠缠着禅法修证的行者。有的修学禅法的人,出现对经教乃至语言文字轻视或者执著的弊端,文益对此一一加以评述。
在文益看来,禅法修证与经教关系的协调,表现是多方面的。文益在《十规论》中,对通教典、明佛理等禅法修证与经教关系相关的范畴,都一一作了说明。
在文益看来,参悟禅法必须以通达教典为基础,禅宗学人只有通达教典以后,才能“明佛意”、“契祖心”,乃至获得参悟禅法的方法。因此,通达教典只是为了能准确掌握参悟禅法的方法而已。文益指出,如果参悟禅法的人不通达教典,只局限于“守宗风”的话,那就“如辄妄有引证,自取讥诮”。但是,如果仅以通达教典为目标,而忽略参悟禅法,又不免“尽是数他珍宝”。所以,文益警诫参悟禅法的人,“后进之徒,莫自埋没,遭他哂笑,有辱宗风”。由此看来,在参悟禅法与通达教典的问题上,文益是主张,禅法参悟必须以通达教典作为前提,而通达教典必须为参悟禅法服务,其中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意思,是十分明显的。
文益还指出,“夫为参学之人,既入丛林,须择善知识(老师),次亲朋友,知识(同学)要其指路,朋友贵其切磋”。就是说,参悟禅法的人还必须亲近善知识,老师可以对参悟禅法进行指导,同学可以相互促进禅法参悟。因为,许多老师和同学,在参悟禅法的过程中,总结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可以具体指导在禅法参悟上如何用功夫。这对参悟禅法的人是一种难得的锻炼(淘汰)。如果参悟禅法的人,不经过老师的指导和同学的切磋,不经历一番锻炼,结果只会“臆断古今”,不明白古人参悟禅法的方法,而产生错误的理解。可见,文益是主张参悟禅法必须有师承传授的,这样,才不致于错解“古今言句”。但是,文益进一步指出,“学般若之人,不无师法,既得师法,要在大用现前,方有少分亲切,若但专守师门,记持露布(死守教条)[25]皆非颖悟,尽属知见”。意思是说,参悟禅法的人,虽然要追随老师学习,但不能恪守和只记住老师的语句,要把老师教导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自如,用平时学到的禅法来指导生活,让生活充满智慧和光明,才算是真正掌握参禅的要领。所以,文益指出,“真丈夫材,非儿女事,切忌承言滞句”。由此看来,文益一方面告诫初进学习的人,既要追随善知识学习,在善知识处得到锻炼,另一方面,又不能执着老师所说的语言文字。足见文益仍是在协调参悟禅法与语言文字的关系。
另外,当时流行用歌颂的形式,来表述自己内心对禅法领悟的风气。文益对此也作了评述。在文益看来,歌颂只不过是方便手段而已,通过这些方便的形式,来协助佛法道理的传播和表达自己对禅法的领悟。因此,文益指出,“宗门歌颂,形式多般……假声色而显用,或托事而伸机,或顺理以谈真,或逆事而矫俗”。宗门作歌颂与普通作歌颂的意义是不相同的,宗门作歌颂,一方面要通晓声律,否则落于俗套。一方面要通达义理,否则所作歌颂被后人传颂,是会贻误后学的。古人以诗言志,就是通过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宗门作歌颂,是借以表达自己禅悟的境界以及对佛教义理的理解。文益本人并不反对作歌颂,他自己也写了大量的歌颂并流传后世[26]。但一定要知道,禅法学人只是通过歌颂这种形式,来传播佛教义理以及表达自己内心领悟的禅法而已,不能为歌颂而歌颂。
从以上文益对参悟禅法必须通达佛典,亲近善知识又不能死守教条,作歌颂但必须目的明确等方面的评述来看,文益想要协调参悟禅法与经教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文益的禅法思想中,“禅教一致”的主张,是贯穿始终的。
(三)宗风圆融
“宗风”,禅宗特殊用语。禅宗自唐末五代,形成各种不同流派,这些流派中,历代祖师禅风相承,形成所谓不同的门庭施设(接引学人的方法),乃至传法方式也有所不同。后世遂把不同流派间的门庭施设及传法方式的差异,说为是各自流派的“宗风”。因此,简单地说,所谓“宗风”,就是不同流派间的鲜明流派特色而已。
其实,不同流派间虽然有门庭施设及传法方式的不同,但是,在遵循禅宗基本宗旨的原则上是不应该有差别的。因此,文益指出,“祖师(菩提达摩)西来,非为自有法可传。以至于此,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有门风可尚者哉!然历代宗师,建化有殊,遂相法讼革”。在文益看来,那些所谓门庭施设等差别,都只是各流派历代祖师的善巧方便,以巧妙的方法接引学人,如何在禅修的过程中进行修持。在遵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禅宗基本宗旨的原则上却是一致的。
文益又指出,自慧能、神秀(606—706)之后,由于宗师见解有所不同,历代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如先有南北二宗[27]。南宗慧能门下出南岳怀让(677—744)、青原行思(?—740),青原行思门下出石头希迁(700—790)的石头宗,从南岳怀让门下出了马祖道一(709—788)及其江西宗。从这两支下,“各分派列,皆镇一方,源流滥觞,不可弹纪”。其中有名者,如“德山、临(原本作林)济、沩仰、曹洞、雪峰、云门”等,各有“门庭施设,品下高提”。但是,各流派形成以后,到了其弟子时代,“不知大道无方,法流同味”,将各流派一致的禅宗基本宗旨抛在一边,过分强调各自流派的宗风,以致形成“斗争以为神通,骋唇舌作三昧,是非等起,人我山高”的局面。
同时文益在《十规论》中还指出:“天下丛林至盛,禅社极多,聚众不下半千”。意思是说,各地寺庙看起来十分兴盛,弘扬禅宗的禅堂(禅社)也不少,以寺庙禅堂为中心的修学者也很多,但真正知道如何参悟禅法的人,是很少的。其中“或有抱道之士,洁行之人,肯暂徇于众情,勉力少于祖席。会十方之兄弟,建一处之道场,朝请暮参,匪惮劳苦。且欲续佛慧命,引道初机”。而绝大多数人,只知道妄为人师,在传法及引导弟子的过程中,“护己之短,毁人之长”,迷惑世人,虚张声势,其实尽是在败坏佛法,而毫无惭愧之心。在文益看来,这实在是宗门之不幸,应提高警惕。这种局面如果任其发展,对禅宗的整体传播是十分危险的。
有鉴于此,文益对各个流派的门庭施设及宗师传法风格,进行了扼要的概括。他说:
凡为宗师,先辨邪正,邪正既辨,更要时节分明。又须语带宗眼,机锋
酬答,各不相辜。然虽句里无私,亦假言中辨的。曹洞则敲唱为用,临济则
互换为机,韶阳则涵盖截流,沩仰则方圆默契,如谷应韵,似关合符。虽
差别于规仪,且无碍于融会。
在文益看来,各流派的宗师,在传授禅法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把握禅宗宗旨(辨邪正),另一方面又要根据不同根机的弟子,巧妙地运用各种方便,通过老师与弟子间充满机锋而又和谐的问答,启迪弟子们对禅法的领悟。在此基础上,曹洞宗则是“敲唱为用”,重视老师与弟子间的问答,乃至理事关系的五位君臣[28]。临济宗则是以“互换为机”,老师与弟子间的主宾地位,是以对诸法实相的认识程度为中心的。教导弟子是采取因根机不同而分别教导的方法。云门宗(诏阳)则是以“涵盖截流”为方法来教导弟子。所谓“涵盖”,即是“云门三句”[29]的第一句“涵盖乾坤”,意思是说宇宙万有都在一实相中显现。所谓“截流”,即“云门三句”的第三句“截断中流”,意思是说引导学人如何在当下一念之中,断除世俗的情欲、观念乃至思维而契证诸法实相。沩仰宗则是以“方圆默契,如谷应韵,似关合符”的方式来启悟弟子,要求老师与弟子在问答之间,必须配合默契、协调。
在文益看来,以上四家流派虽然可以运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来启悟弟子,但禅宗的基本宗旨是不能抛弃的。也就是说,在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基本立场上,允许各流派在教导弟子的过程中,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的是要让弟子能真正的体悟到禅法的真正精神。因此,文益在《十规论》中对那些忘却禅宗基本宗旨,而只知道“党护门风”、“对答不观时节(根机)”、“护己之短”的禅门弊端,提出了批评的意见。
也由此可以看出,文益本人并不反对禅宗流派的形成,并不反对禅宗各流派根据弟子的不同根机而采取灵活的引导方式。但是,在此过程中,绝不能置禅门基本宗旨而不顾,要在禅宗基本宗旨得到贯彻的情况下,流派的形成及门庭施设才是正确的。从文益的这些观点来看,他对“宗风”的态度,是十分圆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