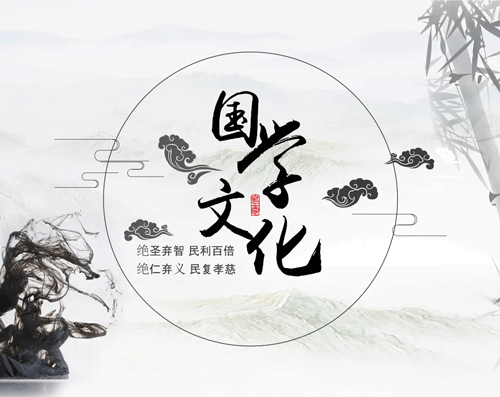异种基因转殖的伦理争议及佛法观点
发布时间:2024-01-17 15:36:45作者:互动金刚异种基因转殖的伦理争议及佛法观点
释昭慧
一、 前言
二十世纪后期,生命科学有了三大突破──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人体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以及体细胞核转殖(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俗称复制:cloning)技术。生命科学的三大突破,产生了巨大的伦理冲突,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生命科学必须审慎地看待其内容,及其相关伦理问题。
本文探讨的是三大生命科学中的一门──基因工程──的伦理争议,特别是异种基因转殖(Transgene, gene transfer, transgenosis)在动物身上实施所引生的伦理问题。
基因转殖技术,就是用遗传工程的方法,以限制?充当手术刀,将生物细胞内的螺旋状DNA(deoxyribonucleic acid, 去氧核糖核酸,亦即动、植物的遗传物质)分子切开,选取所需要的一段基因,与其他相关基因重新组合。经过重组的基因,要藉助于另外一些人为方法,送回生物体内发挥作用。重组 DNA 引入体内,其改变有两种不同分类:一、具有遗传特性的生殖细胞改变,需经过生殖细胞、早期胚细胞或胚干细胞株之体外操作;二、不具有遗传特性的体细胞DNA 之改变,可经由基因疗法,如直接注射质体 DNA或病毒媒介的基因转型方式。
此中,“基因转殖植物”,是指将外源DNA通过载体、媒体或其他物理、化学方法,导入植物细胞,并得到整合和表现的新品种植物。而“基因转殖动物”,则是指通过基因转殖技术,将改建后的目标基因或基因组(genome)片段导入实验动物的受精卵,使其与受精卵DNA发生整合,然后将此受精卵转移到雌性受体的输卵管或子宫中,使其顺利完成胚胎发育。因此后代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基因组内,都携带有目标基因,并能表现外源基因的生物效应。
先简要追溯基因工程发展史:早在1953年,英国剑桥大学华生和克里客(James Watson & Francis Crick)提出了DNA分子结构的双螺旋模型,证实了基因就是DNA分子。自此,遗传学走向了分子生物学,直接从生命遗传分子的结构来探索生命,并为当代生命科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十世纪七○年代,生命科学出现了重大突破,基因工程(也称“重组DNA技术”),通过对基因的剪裁、组合、拼接改造和加工,使遗传物质得以重新组合,然后通过载体,进行无性繁殖,并使新的基因在受体细胞中表达,按照人们预先设计的蓝图,产生人类所需要的物质,以达到定向改变生物性状的目的。
自此,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基因工程把生命科学推进到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它改变了过往生命科学仅用于认识生物和利用生物的局面,而进入到人工改造生物乃至创造新生物的局面。
然而基因工程一经启动,立刻引发了安全上的疑虑。1972年,美国八○年代生物科技产业先驱,美国史丹佛大学教授杰克森与伯格(DA Jackson, RH Symons, P. Berg),将猿猴病毒SV40DNA,与大肠杆菌质粒DNA通过剪切后拼接在一起,人工合成了第一个重组DNA杂交分子。另一生物学家普兰克(Planck)提醒伯格:SV40具有致癌性,倘将带有SV40的细菌大量增殖,有可能会成为传播人类肿瘤的媒介,而产生严重的后果。伯格不但接受了普兰克的建议,停止了自己的研究,而且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伯格信件”,向全世界科学家呼吁:在重组DNA分子潜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尚未找到适当防护措施之前,应自动停止生产剧毒物质基因,对于自然界尚不存在的抗药性组合基因,亦应停止扩增实验,而且应当停止致癌基因的扩增实验。
此一呼吁受到了重视,1976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关于重组DNA分子研究的准则》,对此项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进行管制,要求立即暂停基因重组研究;然而基因工程的研究列车业已启动,势不可挡,因此到了1979年,美国政府还是恢复了基因重组研究。
以基因转殖动物或其产品为直接食品、原料加工生产的食品乃至医药用品,其研究已有数十年历史,但真正商业化则是近二十年间事。1983年,世界上第一株基因转殖作物——一种对抗生素产生抗力的菸草出现。此后大量基因转殖作物陆续出炉,至1996年,美国将部分基因转殖食品(大豆、玉米、油菜、花生和番茄)推上了商业化的进程。
至二十世纪末,基因工程、发酵工程与细胞工程,成为最迅速发展的生物科技,它在动物、植物与微生物的基因改良中被广泛运用,加速了所谓“优良作物”的筛选与培育过程。此中特别是以生物科技为基础的基因转殖食品产业,包括微生物发酵技术的发展、农作物高频再生系统的建立,以及动物无性复制技术、人工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发展,已将遗传改造的动植物,从实验室推进到广袤的农田、畜牧场与超级市场,促使传统农业产生了深远的变革。
基因转殖作物能自己释放杀虫剂与抗除草剂,不但减少了传统化肥与农药对环境所造成的染污,而且还增加了单位面积生产量;基因技术可以使农作物在盐硷地或旱地上生产出丰富的食品,还可以产生防病疫苗与食品。因此基因转殖食品的研发与生产者声称:基因转殖科技能为人类解决人口膨账、食物短缺、能源匮乏、疾病防治与环境污染等问题。
然而反对者却也提出坚强的理由,认为:不能预料基因转殖食品未来会对人体与动物健康产生何等影响,也无法逆料种植基改食品对生物多样化所可能产生的伤害。风险既然无法正确预估,因此不宜将全人类与整个地球当作实验品。
最近出现一则消息,为了回应全球各地的抗议声浪,总部设在圣路易的生物科技农作物先驱孟山都公司(Monsanto)已于2004年5月10日宣布,原拟推出世界前所未见的基因改造(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小麦,已决定暂时搁置该计划。该公司发言人霍纳说,由于春麦耕作面积缩小,小麦农和小麦买方也表示反对,因此孟山都决定暂停基因改造小麦计划。
过往孟山都发展的耐草甘膦玉米和黄豆饲料谷物已成功商业化,并希望以美国和加拿大为起点,把抗除草剂技术引进小麦种植业。因此孟山都实地试种耐草甘膦(Roundup Ready)小麦长达六年,并已投资数百万美元于该项基改计划。耐草甘膦小麦经过基因改造,可耐喷洒孟山都所产的Roundup牌除草剂,作物本身的生长不受除草剂影响。
但这些努力却引起了环保人士、农民、消费者、宗教团体乃至于外国小麦买主的群起反对。他们担心,经过基因改造的小麦,食用后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可能会增强野草的抗药性,甚至让世界重要的谷类作物遭受企业控制。
至于基因转殖的农场动物,目前已有用于食物的部分,如增加猪只的瘦肉比例、增加乳牛的乳汁产量、增加鱼类与禽畜的生长速度等等。科学家对于基因转殖动物在药品制造以及器官移植方面的前景,更是大大看好。
然而近年来让人闻而色变的SARS、禽流感与狂牛症,都来自以禽畜为宿主的病毒,但它们竟都跨越了物种界限,侵入到人类体内,而且致死率极高,迄无有效对治之道。大量牛只、果子狸与禽类动物,因此惨遭“杀无赦”之待遇。这让人们不禁更加质疑:异种基因转殖极有可能自此将许多原属人畜不共的致死疾病,带入人类社会,成为人畜共同疾病。这是基因科技潜伏于人类间最为险恶的危机。
截至笔者撰稿时,以Google搜寻引擎键入“基因转殖”四字,光是中文网页,就已有15,200笔资料,若是搜寻“Transgene”,则更是多达318,000笔资料,显示基因转殖相关资讯非常庞大而丰富。因此本文只在本节之中,扼要说明基因转殖技术的内容,及其简史与近闻;第二节则罗列有关基因转殖在正反两方面的伦理争议,并从效益主义、义务论、基督宗教的神学观点与佛教的缘起论,分析几个异种基因转殖科技的伦理争议。这包括了:
一、 人工改造生物乃至创造新生物的伦理争议。
二、 人类基因植入动物体内所产生的伦理争议。
三、 动物基因植入植物受体所产生的伦理争议。
四、 基因转殖技术在动物实验过程中的动物处境。
五、 动物受术之后畸型或夭折的处境。
六、 基因转殖潜在的人类危机与生态威胁。
动物的异种基因转殖,紧接而来的就是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本文将于第三节中特别针对此一部分的争议,提出佛教伦理学的观点。
本文结论之中,除了综述全文观点之外,并分析科技“价值中立”的迷思,以及当代基因科技在社会体系之下,或隐或显地依其价值观以操作其间的事实。由此看待科技界与伦理界有关基改工程的争议,即能体认其更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基因转殖科技的伦理争议
(一) 基因转殖植物
作为一门生命科学,基因转殖技术可以选择性地删除或加入一个已知的基因,这提供了生物学上种种问题的探讨方式,也开拓了广大的应用空间。
目前用来生产基因转殖植物的方式总共有十余种,若按转型体系的原理进行分类,则可分为三大类型:
1.不用任何载体,通过物理、化学方法直接将外源基因导入受体细胞的直接转型体系。
2.以生物体为载体的转型体系。
3.以植物自身的生殖体系种质细胞(如花粉)为媒体的转型体系。
用于植物性基因转殖食品的目标基因包括:
一、抗虫基因:虫害是农作物减产的一大要素。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因虫害所造成的损失,约占农作物总收获量的13%,每年约损失数千亿美元。而化学防治所造成的环境与食物污染,迄无改善可能。因此,使用基因工程,将抗虫基因引入农作物细胞,使其在寄主细胞内稳定地遗传与表现,从而培育出抗虫作物新品种,就成了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抗虫基因有许多种类,目前最常使用的是从微生物苏力菌分离出来的杀虫结晶蛋白(insecticital crystal protein, ICP)基因,简称Bt基因。抗虫基因在理论上有以下优点:
1. 保护作用有连续性,可控制任何时期内发生的虫害。
2. 只杀害摄食害虫,对非危害性生物没有影响。
3. 整体植株,包括化学杀虫剂很难作用的部位(如下表面与根部),均可受到保护。
4. 抗虫物质只存在于植物体内,不存在染污问题,且较诸化学杀虫剂减省费用。
5. 与发展新型杀虫剂相较投资较少。
二、抗病基因:农作物损失的三分之一来自病毒,故抗病基因转殖植物亦是农业增产的良好品种。
三、耐除草剂基因:现代化农业通过化学方法来控制杂草,但那些除草剂也同时能伤害作物,因此其应用有所限制。通过基因工程将耐除草剂基因导入现有作物品种,不仅扩大了现有除草剂的应用范围,而且还影响新型除草剂的设计与使用。
四、抗逆基因:这包括抗低温基因与抗旱、抗盐基因,将使得寒冷天候与干旱地区,以及贫瘠的盐硷地,都能种殖含有上项转殖基因的新作物。
五、果实保鲜基因:果实熟化过程迅速,常常导致腐烂,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该类基因使果实保鲜期被明显推迟,而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效益与应用前景。
六、改良作物质量或产量之基因:包括提高作物产量、改良种子蛋白质成份与油脂品质等。
然而基因转殖植物也并非没有安全性考虑。这包括:
一、基因转殖植物在田间栽种后,有可能在环境中成为不可控制的杂草。
二、基因转殖植株与非基因转殖植株之间,有可能出现花粉传递,从而导致标记基因转入不同作物中的失控现象。
三、引起病虫害的病毒或昆虫,会随着基因转殖植物的抗性,而逐渐产生适应力,使得作物失去了对病虫害的抗性。
四、迄今为止,吾人并无把握,这类基改植物在人类长期食用之后,是否会对人体产生伤害或遗传性的影响。
五、迄今为止,吾人亦无法预估基改作物在田间栽种,是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六、基改食品中之蛋白质过敏原,有引起食物过敏的可能性。
七、基改食品中之毒素(如蛋白?抑制剂、溶血剂或神经毒素等),虽可增强基改作物的抗性,却有可能带来安全性的问题。
(二) 基因转殖动物
基因转殖动物是指基因组中整合有外源目标基因的一类动物。通过基因转殖技术,将改建后的目标基因或基因组(genome)片段导入实验动物的受精卵,使其与受精卵DNA发生整合,然后将此受精卵转移到雌性受体的输卵管或子宫中,使其顺利完成胚胎发育。因此后代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基因组内,都携带有目标基因,并能表现外源基因的生物效应。
目前已发展出来的转殖技术将近十种,但最常使用的转型方法有下列三种:
1. 反转录病毒载体法:利用反转录病毒(如农杆菌)感染胚胎的胚叶细胞(blastomeres)。但由于反转录病毒载体所能携带的外源基因大小有限,不能大于10Kb,而且载体DNA所需的辅助病毒基因组,也有可能会与目标基因一起整合到同一细胞核中,而形成基因转殖动物的病毒污染,因此它不是产生基因转殖动物的主要方法。
2. 受精卵显微注射法:利用显微注射的方式,将重组过的DNA直接注入受精卵的原核中。由于大到数百Kb的DNA片段,都可用此方法送入受精卵中,因此,这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方式,也是用来产生异种基因转殖动物的方法。
这些插入的转殖基因,由于插入的位置并不能事先测得。因此,有的可能出现数个复制的外源基因,同时插入同一位点的情形,从而干扰着基因的正常表现,影响基因转殖动物的正常发育与代谢;有的个体可能因基因插入位点不合适,而无法表现产物;有的个体基因复制过多而导致表现过量,干扰自身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每一个原种转殖基因的动物(founder animals)必须建立起它自己独立的转殖基因动物株(transgenic line)。显见此种方法依然有其重大限制。
3. 基因操控(genetic manipulation)法:藉由基因标的的方式,将重组DNA片段转入培养的胚胎干细胞(ES cells)中,以对原本染色体上的基因进行替换改造。作为载体的胚胎干细胞,来自于囊胚中的细胞团(inner cell mass),在特定的培养下,它们可以增生,并且维持可变成体内任何器官的能力。最后,再将处理过的胚胎植入假孕的代理孕母(pseudopregnant surrogate mother)体内。
用于动物转型的基因,至今已生产出基因转殖家禽、家畜、啮齿类、鱼类、昆虫等多种属动物。它的效用包括:
一、提高动物的生产性能:如转入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 GH)基因的基因转殖猪,其成长速度较快,饲料利用率提高,瘦肉比例增加,较符合饲养者与消费者的利益。
二、提高动物产毛性能:如以类胰岛素IGF-I基因植入后,羊之产毛量平均提高了6.2%。
三、提高食用肉质量:增加家畜食用肉品的蛋白质,减少脂肪含量。
四、提高乳汁分泌量与营养含量:使牛、羊乳汁增产,营养提高,或是获得自然情况下所不具备的营养成份。
五、提高抗力:如将抗冻鱼蛋白植入温带鱼种体内,可增强其抗寒能力。其他抗病、抗旱、耐环境压力之生物性状,亦可透过基因转殖技术而提高。
六、利用基因转殖动物以生产基因工程药物:利用牛羊等乳腺作为生物反应器,从基因转殖动物的乳汁中获取目标基因产物,不但产量高、易纯化,而且由于表现的蛋白经过充分的修饰加工,具有稳定的生物活性。由于细菌基因工程需要很大的发酵槽,细胞基因工程需要很多昂贵设备来培养细胞,而若使用基因转殖动物,只需养活它们并使其持续繁殖即可,投资成本低、药物开发周期短、经济效益高。此时产乳动物宛若一座大型制药厂。这是生物医药产业生产药物的新途径。
七、 提供异种器官移植的丰富来源,解决全球器官供应短缺的问题。
但反对者对于此诸基改工程,抱持审慎怀疑的态度(前四点理由与对基因转殖植物的顾虑相同):
一、迄今为止,吾人并无把握,这类基改动物在人类长期食用之后,是否会对人体产生伤害或遗传性的影响。
二、迄今为止,吾人亦无法预估基改动物的繁殖,是否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三、基改食品中之蛋白质过敏原,有引起食物过敏的可能性。
四、基改食品中之毒素(如蛋白?抑制剂、溶血剂或神经毒素等),虽可增强基改作物的抗性,却有可能带来安全性的问题。
五、反转录病毒载体DNA所需的辅助病毒基因组,有可能会与目标基因一起整合到同一细胞核中,而形成基因转殖动物的病毒污染
六、异种基因转殖,特别是人与动物之间的基因互换,有可能会使得原属动物特有的病毒,因其基因变造而侵入人体,形成人畜共通疾病,这将带来无法想像的人类浩劫。狂牛病、禽流感与SARS所带来的灾难,让人们更加审慎看待基因转殖科技在这方面的潜在危机。
(三) 基因转殖科技所带来的宗教难题
异种基因转殖不但引起俗世伦理学界的若干质疑,同时更带来了宗教伦理层面的困惑。前述对基改动物与基改植物之种种质疑,由于攸关人类、土地、生态环境的安危,当然同样受到各种宗教的质疑。
除此以外,宗教界所特有的伦理疑虑如下:
一、基改食物使某些宗教信徒可能会误食禁用品。例如:将猪的基因转入牛中,使得伊斯兰教徒可能误食猪肉而不自知。将动物基因转入植物中,可能使包括佛教徒、一贯道道亲与动保人士在内的素食者,深受困扰。
二、将人类基因转入动物以制作食品、药品乃至人类器官,或是采用含人类基因的生物体作为动物饲料,则该动物与生物体将混淆了人类的独特性,这对以人为“位格”之存在的基督神学,已构成了一项难题。亦即:利用“它们”到底有没有侵犯人的神性?
三、由于基督宗教是创造论,主张唯神能创造万物,所以基因转殖以制造新种动物或植物,在某些严格诠释“造物”角色的神学家看来,都是在干犯着神的权力,扮演着“上帝”的角色。
四、包括基督宗教或道家思想,都重视“自然”的价值。因此类似“干犯上帝”的指责是,基因转殖“违反自然”。
然而什么是违反自然?人类的疾病治疗、生态控制、连体婴分割、兔唇矫治、变性手术等等正面贡献,岂不也都是都违反自然吗?“违反自然”的定义与范畴,显然不容易厘清。再者,对于无神论者或非基督徒而言,如果连“神是否存在”都已不能肯定,如何能信服“人有神性”或“人创造新生物,就是干犯上帝的权力”的这类说法呢?
至于人的独特性,就俗世伦理而言,或许并无依“神性”以证成的必要,只要证明人有动物所不具足的“理性”,即可划出一条保护人类的底线了。然而这种判准,却无法获得佛教与动物解放运动者的共识。
基改作物确实会让宗教信徒产生误食禁用品的困惑。但吃了含有动物基因的植物,是否就等于佛教所定义的“杀生”?此则另当别论,因为杀生必须是使动物的命根断除,而动物基因并不等同于动物生命,在有取识(梵sopadana-vijJAna)不执受的情况下,动物基因植入植物受体内而被人摄食,是不会引生植物痛楚的。
因此,宗教伦理与俗世伦理最有交集的部分,可能还是前述对基改科技攸关人类、土地与生态环境的安危之种种质疑。
(四) 基因转殖科技的伦理探索
笔者先前所陈述的,有关基因转殖科技所引生的争议,就俗世层面而言,争议两造都不约而同使用着伦理学中效益主义(Utilitarianism)的理论,亦即“最大化效益原则”。所不同者,只是两造对“何者方为最大化效益”的认知。由此亦可看出“效益主义”的瓶颈,亦即:
一、无论是就质还是就量以观,吾人都无法确证,推动基改与反对基改,何者方能真正达到“最大化效益”。
二、吾人对大自然整体的所知尚少,基因工程所面对的不确定因素也很多,更且以有限因缘来微观生物分子,当然无法宏观整体宇宙的无限时空。因此,即使基因转殖科技在眼前确实带来了人类在作物、粮食、医药等等方面的庞大效益,效益主义依然不免要接受如下的质问:究竟要将视界拉开到多广的面向,延展到多长的时间,方能真正看出“何者方为最大化效益”(或“何者方能带来最小量伤害”)?
义务论的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基因工程伦理思辩方面,依旧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义务论者惯常揶揄效益主义“是否为了拯救众人而可枉杀一个无辜”。确实这种“枉害无辜”的案例,在基因转殖食品、药品的人体实验及产品推广过程中,并非鲜见。也因此,义务论依然在这场基因革命的拉钜战中,有着“中流砥柱”的重要性。基改科技公司与科学家不得贸然以“人”为新品种基改食品的研究对象;不得使用“最大化效益”原则,来合理化其使少数无辜者受害的种种过失,而必须负担起赔偿责任。凡此种种相关规范,都可看出:在一片“效益”取向的氛围底层,还是有一处“禁区”(an off-limits area),是无论有多大效益,都碰触不得的。
(五) 基改“禁区”的佛法观点
然而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争议性的看法:“最大化效益”所利及的对象,或是“己所不欲”所不可转施的对象,是仅止于“人”,还是可扩大而涵括“人”以外的其他动物?
基督宗教基于“人具神性”的理由,俗世义务论基于“人具理性”的理由,都可合理主张,基改“禁区”的底线仅及于“人”。然而若依佛法,却是将底线扩大到“含灵蠢动”的一切众生。
依佛法的缘起(梵prat?tya-samutp?da,巴paticca-samupp?nna)论,基改工程所潜在或浮现的(伤害少数族群、伤害人类、破坏土地、改变生态等等)负面因缘,当然应予重视。但是缘起论必将推演出“护生”原理(这在笔者的《佛教伦理学》与《佛教规范伦理学》中业已详加阐论,兹不重赘),因此,在这一波接一波浪潮汹涌的基因革命中,动物的艰难处境,亦应给予强烈的关注。
一、佛家是业感缘起论,而非一神创造论,此一无神论的主张,自不可能赞同人有特殊的“神性”可言。

二、人具有“理性”的命题并不周延,这可能会让智障者、婴儿、胎儿、胚胎,乃至“人鼠”、“人猪”之类含人类基因或人类胚胎的动物,因其不具全分“理性”,而在这场基改革命中,沦为最大的牺牲品。
三、依其缘起性空论,认为众生(包括动物在内)皆为因缘生法,因缘条件和合则生,因缘条件离散则灭,此中无有常恒不易、独立自存而真实不虚的自性(梵svabh?va,即本质:substance)可言,故“人”或“猫”、“狗”、“鸡”、“猪”等之形体虽暂有异,但一律随因缘迁化而往覆升沉,尊卑贵贱之阶位不恒存在;升沉其间的规则相同,终归坏散的结果相似。佛家即此“法性平等”,而推出了“众生平等”的结论。
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同理心,佛家名为“自通之法”,此同理心之自然流露,关切的会是所有具足“觉知能力”的生命。故佛法不依“理性”,而依“觉知能力”以为禁区底线的判准。
然而若将动物纳于基改“禁区”,在实际操作层面马上就会遇到困难。例如:
一、截至目前为止,动物实验仍是评价基因转殖食品安全性时,不可替代的手段。而且目前与基因工程有关的动物实验,几乎占了全部动物实验的80%。若要顾虑所谓的“动物处境”,岂不是让所有的基因工程停摆?
二、截至目前为止,被转入外源基因的动物,死胎与畸型率较高,畸型发展使存活动物备受痛苦煎熬,这可能与外源基因进入受体后,与受体染色体基因组随机整合,调节失控、遗传不稳定等因素有关。若要顾虑所谓的“动物处境”,岂不是让所有的动物基因转殖工程停摆?
三、异种基因转殖还有一项医学前景,就是含有人类基因或人类胚胎之异种器官拿来移植人体的可能性。在器官需求孔急而器官来源鲜少的现实情状之下,若要顾虑所谓的“动物处境”,这不但严重违背学界与医界利益,也必将违反人类利益。
然而,即使被讥为“陈义过高”,佛弟子对异种基因转殖所带来的动物处境,也都不能无动于衷。而必须依“缘起论”以作中道实践,亦即,就见闻觉知的有限因缘,无私而勇敢地,尽己所能以制造一些让动物处境更为社会所关切、更为法律所保护的因缘条件。
二、 异种器官移植的佛法观点
1990年,美国纽约医学院教授斯塔尔特·纽曼(Start Newman)提出了制造“人鼠”的设想,即将老鼠的胚胎细胞注射到人的胚胎里,或把人的胚胎细胞注射到老鼠的胚胎里,制造出兼具人和老鼠细胞特性的生物。
这种含有人类基因的老鼠(人鼠),由于其免疫系统与人体的免疫系统相同,因此,给这些“人鼠”注射某种人类疾病的蛋白质时,其体内会?生抗体,利用这种抗体,可以加快新药的研制,并制造出不受人体免疫系统排斥的新药。已有两家公司,利用基因改造过的“人鼠”,成功研制了许多新药。这些新药虽然还没有上市,但其前景普遍被看好。
其次,由于过往大都以小白鼠进行药物试验,但老鼠毕竟不是人,其试验效果不能完全等同于人体试验。轻易做人体实验,又面临着重大的伦理争议,因此,异种基因转殖技术所创造出来的“人鼠”,也有药物试验方面的需求。
纽曼教授以其所创“人鼠”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专利和商标,这让专利局甚感为难,因为过去二十二年来,它虽对一些活体器官(包括人类基因与细胞)制造,以及含有少量人类DNA的动物,给予专利权,但专利局在批准这类专利时,有其法律底线:人类胚胎和人不能给予专利。它的法律依据是“专利法”,以及禁止奴隶蓄养贩卖的宪法第十三条。专利局拒绝了这项“人鼠”专利的申请,因为它“包含了人体”,而人体是不能授予专利的。当然,人类胚胎与含有人类胚胎基因的“人鼠”是否相同,这还是有争议的。(何洪泽,2002)
“人鼠”这项异种胚胎移植术,并非独例,更多“拟人化”的基因猪,也已陆续出笼。因为这些基因猪的器官,在模拟的人体环境中,已经突破了超急性的排斥现象。由于猪器官与人器官较为接近,且猪的繁殖力强,容易饲养,用猪器官进行人体移植研究,不会像用灵长类动物进行实验那样引起广泛争议,因此,转殖基因复制猪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往后猪器官移植到人体的前景很被看好。而且异种器官移植,是短期内解决全球性移植器官短缺的唯一可行途径,仅出售供人体移植用的猪器官,就有50亿美元的市场,如再加上细胞治疗,人猪之间的异种基因移植,将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动物的异种基因转殖,必然会引生异种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这是因为“楚人无罪,怀璧其罪”,植入人类基因的动物,因其“怀璧”而被觊觎。若纯从人类本位的医学伦理来看,异种器官移植,是以活体动物器官,用供病人生命之存活,这不但可解决器官供应量不足的问题,而且较诸人体“脑死”之后的器官移植,所引起的伦理关注或许更少,因此异种器官移植,是并没有抵触各种生命伦理原则的。孙效智教授于此分析云:
首先是“当事人自主原则”(autonomy),其次是“不伤害原则”(nonmaleficence),再其次是“造福原则”(beneficence)。任何医疗行为都必须尊重当事人(或其家属)的自主性,故必须以病人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为基础。“知情同意”是说,病人的同意必须是在充分瞭解各种医疗选择的利弊得失之后而为之的“同意”。“不伤害原则”与“造福原则”可以合在一起看,也就是说,医疗行为应该造福病人,其所带来的伤害不应大于它所带来的好处。当然,若伤害是无可避免的时候,合乎伦理的行为必须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那一方,因此这又可以称为是“较小恶原则”(lesser evil principle)。(孙效智:2002)
孙教授依此诸原则检视异种器官移植问题,认为,其伦理争议不算太大。质疑其伦理意涵的主要论述,集中在担心此种技术的副作用或后遗症上面,例如:
质疑一、将原属于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类,或将寄宿在动物身上的病毒转移到人身上,这恐将会引起毁灭性的灾难。——孙效智认为,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也是异种移植所必须面对的最严肃之伦理挑战。倘若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充分而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么,即使科技上异种移植可行,在伦理上它仍然是不可行的。
质疑二、接受动物脏器,对于病人心理有可能会形成负面的冲击。——孙效智认为,病人心理是否能接受的问题,这不该由旁人来置喙,而该看病人的意思。
质疑三、由于同种器官移植,有时会发生接受移植者显示出器官供给者某些特征的现象,因此有人担心,异种移植是否会让病人失去某些人性,例如出现“猪头猪脑”之类的异种特征?——孙效智认为,这一方面要看病人及其家属在“知情”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即“当事人自主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看在“缩短生命”与“气质变化”的两难之间,何者较符合“较小恶原则”。就这点来说,除非“气质变化”的问题大到丧失人性或失去人格的地步,延长生命似乎仍是较小恶的选择。
质疑四、所谓异种的动物若很接近人类,例如黑猩猩,那么,在动物伦理上是否经的起“物种主义”的批判,也是不容忽视的课题。——孙效智认为,现在异种移植研究已较少使用灵长类,而多改采用猪只,这使得物种主义的质疑几乎不再存在。(孙效智,2002)
但上来所述,无论是质疑还是回应,都是在宗教神学或俗世哲学中“人类本位”的思维框架下进行的。即使孙教授带到了生命伦理或医疗伦理中的“当事人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造福原则”与“较小恶原则”,但这依然是在人类中心主义前提下的“不违原则”而已,它似已预设了“动物不等于生命”的前提。依佛法以观,则吾人不免要提出如下质疑:
质疑一、异种器官移植,有经过基因猪等“当事猪”的知情同意吗?若无,这是否依然违背了“当事人自主原则”?
质疑二、异种器官移植,有顾及基因猪等自身生命的福祉吗?这种医疗行为对基因猪,能看得出任何大于伤害的好处吗?若无,这是否依然违背了“造福原则”与“不伤害原则”?而这又岂符合生命伦理中的“公正原则”?
质疑三、异种器官移植,对器官受体的人类而言,只是要在“缩短生命”与“气质变化”的两难之间,比较出何者较符合“较小恶原则”,但对基因改造的猪只而言,则完全只有“终结生命”之一途,又从何以论其“恶之大小”呢?
质疑四、也许论者会说,移植则动物死,不移植则病人死,在动物与病人之间,吾宁取令动物死而病人活之一途,这依然符合“较小恶原则”。但请问:何以证明让动物为人而死,是伦理上的“善”或“较小之恶”?是人的“神性”,还是人的“理性”?如前所言,这些用以证明人类优位的论据,都有其辩证上的漏洞。
质疑五、孙教授认为,倘用黑猩猩作异种移植,容或会遭“物种主义”的批判,但现在异种移植研究已较少使用灵长类,而多改采用猪只,这使得物种主义的质疑几乎不再存在。然而为了人类利益而牺牲猪只生命,这难道不是对猪只的物种歧视吗?不采用灵长类动物,就能避除“物种主义”的责难吗?
总的来说,趋乐避苦、好生恶死的本能,致令人类百般挖空心思,谋求延生之道,异种器官移植科技发展的动力在此。然而动物同样有趋乐避苦、好生恶死的本能,为何就必须为了成全人类的这种本能,而被剥夺其本能之欲求?
也许完全将动物的利益等同于人的利益,有其施行层面的实际窒碍,但完全将人的利益凌驾于动物利益之上,而且视为理所当然,这将导致人类更缺少反省其物种歧视心态的机会,也将制造更多残虐动物的“基因奇迹”,因此佛法的“众生平等论”,容或陈义过高,但在人类沙文主义弥漫的气氛之下,以佛法观点来看待基改列车中的动物处境,最起码也是一种“生态平衡”吧!
四、结论
(一) 综述基改伦理争议
综上所述,回顾本文伊始所罗列有关基因转殖技术的六项伦理争议:
一、 人工改造生物乃至创造新生物的伦理争议:由于涉及创造论,因此这是基督宗教神学所较为关注的问题,但俗世或佛教伦理学则不于此置评。
二、人类基因植入动物体内所产生的伦理争议:这依然是基督宗教神学所特为关注的问题,理由是人的“独特性”或“神性”,但俗世或佛教伦理学较不于此置评。佛法关切的是那些动物受术以后的处境。
三、动物基因植入植物受体所产生的伦理争议:这特别会引起伊斯兰与素食者的关注,佛教徒既是素食者,自不可能不关切及此。但吃了含有动物基因的植物,并不等于“杀生”,因为动物基因并不等同于动物生命,动物基因在植物受体内被人摄食,也不会引生植物的痛楚,因此无法依“觉知能力”之判准,而论断摄食者造就“杀业”。
四、基因转殖技术在动物实验过程中的动物处境:这在俗世观点与神学观点,都会视作“无恶”或“较小之恶”,但佛法则反对此种观点,佛法与动物解放运动者的理论容或有些小差异,但都依于“觉知能力”之判准,而认为应减除动物的痛苦,照顾动物的福祉,并尽可能平等考量动物的处境。
五、动物受术之后畸型或夭折的处境:准前第四点可知。
六、基因转殖潜在的人类危机与生态威胁:各种俗世伦理或宗教伦理的系统理论容或不同,但都不能不关切此一问题,这可说是所有伦理争议中的最大共识。
(二) 谁的最大化效益?
基因转殖科技所带来的争议与冲突,方兴未艾。基因转殖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严密结合。严格而言,科学与技术是有所区隔的。科学追求的是“真实”,技术追求的是“效用”。过往科学家认为,科学与技术都是价值中性的,与伦理无涉。依佛家而言,这确是“工巧无记”,非善非恶乃至不会覆障清净解脱,故名“无覆无记”。
科学家往往认为,科技的研究,无所谓伦理问题,让它发生伦理问题的是那些将科研成果作不当之使用的人。然而从前述基因转殖科技研究的内容来看,科技方法、科技活动、产品制造、行销、运用与回收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无法规避伦理问题,而且明显地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的因素,以及个人主观价值的影响。
表象上而言,基因转殖科技所产生的动植物食品、药品乃至器官,似乎符合伦理学上的效益主义——在生命科技中追求“最大化效益”。但吾人依然要进一步追究,这是“谁”的最大化效益?科技研究者的,农场主人的,生物企业的,国家的,人类的,动物的还是生态环境的最大化效益?这一追问,答案招然若揭。
如前所述以观,动物的效益,在这场基改革命中,早已被排除在伦理考量之外。因为任何基因工程都必须经过动物实验,以确保其对人类社会的危险性减到最低。基因工程更试图透过动物异种基因转殖,以研发新的肉品、乳品、医药成品与器官来源。
进以言之,即使暂置动物效益于不顾,而将科技“禁区”的底线设定为“人类”,但吾人依然要质疑:主导整个基因转殖科技的,难道只有“人类本位”的价值观吗?虽然相关企业一再声称这是当前解决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疾疫防治与器官短缺的唯一妙方,然而在操作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国家、企业与学界(亦即:产、官、学三界)在寻求其共同最大化效益的斧凿痕。此从如下近例更可明显判断,基因转殖科技到底符合谁的利益!
由于欧洲民众担忧基改食物会造成环境影响及食品安全,欧盟自一九九九年起,暂停新基因改造产品之销售许可。美国、加拿大及阿根廷为了将基改成品推广到欧洲,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乃不惜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控诉。二○○四年五月十九日,欧盟执行委员会终于取消了五年来饱受争议的基因改造,许可瑞士生技公司Syngenta进口一种经过抗虫基因改造的甜玉米BT-11,这种甜玉米罐头将可进口十年,但是必须明确标示“内含基因改造产品”。
即使欧盟已经做了这样的让步,但美国驻欧洲发言人坎普,在对这项突破性发展“表示欢迎”之外,还是表示,BT-11甜玉米获得通过,并不代表着生技暂时禁令的结束,因此美国WTO对欧盟提出的控告仍将继续,因为单是许可一种新基改产品,无法消除美国的顾虑。
事情显然很清楚:欧洲并非类似卢安达、衣索匹亚、阿富汗等因天灾或战乱而导致饥荒或缺粮的地区,它在农产品方面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即使进口部分粮食,也毋需指定基改食物。因此将基因转殖食品强制推行于欧洲,其理由显然不在于冠冕堂皇的所谓“人类利益”,而是国家商贸利益、生技企业利益与生物科学长远发展的利益。
何以如此?原来当代科学的体制化和研究者的职业化,已使科学技术愈益受制于人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而科学研究领域极为宽广、研究方式也趋于复杂,这使得科学技术成为一种国家政府或企业财团支援的事业,于是,科技的研究领域、研究项目,科技产品的开发、生产、行销等等,均是由政府或企业投资并实施管控的,研究成果自将按照社会价值体系的标准,以进行评价。
这时,科学研究的效用与功能,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因此,在诸多基因工程之中,具有军事或商业方面之潜在利益的基因转殖科目,会被格外重视,并被挹注以大量资源,而这又为该项基改科目之研发、生产与制造,提供了丰厚的利基。一项基改科目研发与否,必当着眼于其投资报酬率。为了获取生技研究人员、生技开发公司乃至生技发展先进国的“最大化效益”,因此要牢牢握紧“利益独享”或“利益有限共享”原则,尽其可能地维护其科研生产的“专利权”与市场利益。那么,在面临“个人利益”与“人类利益”的冲突时,倘无伦理与法律的监督机制,吾人实不难想像,他们会作何选择。
(三) 另一种生态平衡
如前所述,基因转殖技术并非没有正面贡献,但在目前的官、产、学共生系统中,即使它声称照顾的是广大人类的利益,然而在实际表现中,它照顾到的往往却是官、产、学界的共同利益。而伦理学界与宗教伦理学界,则较能跳开此一局限,审慎看待基因转殖对人类、土地、动物乃至生态系统的深远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有了伦理学界与宗教伦理学界的制约,即使部分观点陈义过高,但是“矫往”容或必须“过正”,才够得上力道;最起码让“科技独大”的局面,有着适当的“生态平衡”,这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民九三、六、五,完稿于尊悔楼
──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于“第四届生命伦理学国际会议”